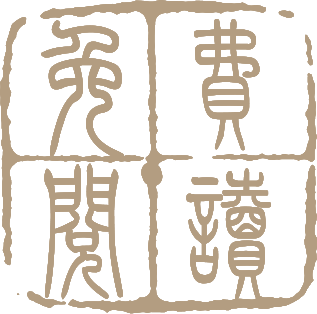
|第三章|
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
一、回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
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,传说不一,至今尚无定说。在各种记载中,有的说是在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的,有的说是唐朝武德年间传入的;有的说是贞观年间传入的,也有说是永徽年间传入的。在中国的史籍中,关于阿拉伯回教的记载甚多,但很少说明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。最早的记载,是见于唐杜环《经行记》中,惜此书已佚,只在杜佑《通典》中保存其一二。
杜环是杜佑的族子,天宝年间曾随高仙芝的军队西征。后高仙芝被阿拉伯人打败,杜环亦被俘虏,居西域十二年,乃从海道由广州归国。他记述阿拉伯的回教情形如下:
大食,一名亚俱罗,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……无问贵贱,一日五时礼天,食肉作斋,以杀生为功德。系银带,佩银刀,断饮酒,禁音乐……又有礼堂,容数万人。每七日,王出礼拜,登高坐位众说法曰:人生甚难,天道不易,好非刼窃,细行漫言,安己危人,欺贫虐贱,有一于此,罪莫大焉。凡有征战,为敌所戮,必得升天,杀其敌人,获福无量,率士禀化,从之如流。法唯从宽,葬唯从俭。……
又谓:
陆行之所经,山胡则一种,法有数般,有大食法、有大秦法……其大食法者……不食猪、狗、驴、马等肉,不拜国王父母之尊;不信鬼神,祀天而已。其俗每七日为一假,不买卖,不出纳。
其次《通典》中的《大食传》,与《新、旧唐书》中的《大食传》,皆大致相同,但皆说永徽二年(西纪六五一年)大食始来朝,也并未说到关于传教的事。在中国的史籍中,最初说到回教传入中国之时期的,则为《明史·西域传》,其中有谓:
隋开皇中,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尔斯,始传其教入中国。迄元世,其人遍于四方,皆守教不替。
这乃是中国正史中第一次关于回教传入的记载。但此是错误的,其错误的来源:第一,是根据西方清真寺王鉷所撰的《创建清真寺碑记》;第二,是根据一般回教徒书籍中的记载。《清真寺碑记》原文:
窃闻俟百世而不惑者,道也;旷百世而相感者,心也。惟圣人心一而道同,斯百世相感而不惑。是故四海之内,皆有圣人出。所谓圣人者,此心此道同也。
西域圣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,居天方之国,其去中国圣人之世之地,不知其几也?译语矛盾,而道合符节者,何也?其心一,故道同也。昔人有言:千圣一心,万古一礼。信矣!但世远人亡,经书犹存,得于传闻者,而知西城圣人,生而神灵,知天地化生之理,通幽明死生之说,如沐浴以洁身,如寡欲以养心,如斋戒以忍性,如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。
至诚不息为感物之本,婚烟则为之相助,死丧则为之相送,以至大而纲常伦理,小而起居食息之类,罔不有道,罔不立教,罔不畏天也。节目虽繁,约之以会其全,大率以化生万物之天为主,事天之道,可以一言而尽,不越乎寻心之敬而已矣。殆与尧之“钦若昊天”,汤之“圣敬日跻”,文之“昭事上帝”,孔子之“获罪于在,无所祷”,此其相同之大略也。
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,足征矣。圣道虽同,但行于西域,而中国未闻焉。及隋开皇中,其教遂入于中华,流衍散漫于天下,至于我朝天宝陛下,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,而立教本于正,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,董理匠役,创建其寺,以处其众。而主其教者,摆都而的也。其人颇通经书,盖将统领群众,奉崇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,而祝延圣寿之有地矣。
是工起于元年三月吉日,成于本年八月二十日。吾等恐其世远遗忘,无所考证,遂立碑为记,以载其事焉。时天宝元年,岁次壬午,仲秋吉日立。
照此碑文看来,可疑之点甚多。
第一,穆罕默德氏生于西纪五七〇年(亦说571年),当陈宣帝太建二年,卒于西纪六三二年,当隋大业六年。隋开皇中,则当西纪五八一年~六〇〇年。在此期间,回教还没有创立(穆罕默德四十岁时始创回教),怎样会传到中国来,并且还流衍散漫于天下,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吗?
第二,碑文中“天方”及“谟罕默德”的译名,也不是唐时所用的译名,“天方”与“谟罕默德”的译名,殆见于元末明初,在唐朝的时候,皆译为“大食”与“摩诃末”。这也是一点可疑的地方;
第三,回教是一神教,保守性、排他性都特别的强。当初传到中国的时候,决不会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妥协。而在碑文中则有纲常伦理、修身养心等名词,与儒家的思想,似乎要达成一片。其实,回教与儒家思想妥协的时期,是在元、明两代,如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建孔庙,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中所记回人尊孔事。元代回教徒之成为儒家,明、清两代的回教徒著作,皆可为明证。在唐朝的时候,决不会如此的。
从以上三点看来,此碑为后人所伪托无疑。所以《明史·西域传》的记载,也是以讹传讹了。但此碑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产物呢?Issar Masen断定是西纪一三六九年(明洪武二年)之后的产物。他以为寺,或者早就有了,以后时常重修。有一次是在明洪武朝(西纪1368~1388年)修建,此碑或者就是成于此时。
陈垣氏亦认为此寺是明时所建。他以为唐时著名的人物很多,王鉷的声名并不甚著,明人作伪所以托治王鉷者,因王鉷在当时曾舍宅为观,此碑或即王鉷舍宅为观时所建。后来此观入于回教人之手,乃就原碑磨改为回教寺碑,而且用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衔名入石。总之,此碑绝非唐时产物,碑文上所载的事实,亦极不可靠。
此外,在中国回教徒的著作中,尚有许多记载,也都说是从隋朝传入中国的。如《天方正学》中谓:
赤尼隋文帝遣使至,欲穆罕默德东,不可,亦遣使赛尔帝在各师率从者百余人东,越岁而还。
在《清真释疑补辑》中,更有类是神话记载,谓:
当隋文帝时,天见异星于西方,帝遣使臣访之,知天方生圣人,求之人中华弗许,圣乃使宛噶斯等,由南海达广东,备述圣意。帝深嘉之,因建怀圣寺于粤东。至今有天方圣使宛噶斯墓,在广州北郭三里许。
在《至圣宝录》中,也有像这样的一段记载,惟时期则不相同。其文如下:
圣人于海拉山默祷其神,显示变化,令一“月”分而为两,旋复合而为一,于是智愚共信,遐迩服从。在中国,盖武德四年(西纪621年)……篆开元通宝以志其异。厥后,太宗梦与圣人接,悚然而寤,乃遣使数辈至其国。圣人乃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,以真经三十藏,计锁勒百十四篇,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,云诵此经能灭诸邪。太宗撰之,颁诸天下,而其教遂大行中土焉。
在这段记载中,说回教是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的,以其时考之,当较前说为可靠。又明何乔远《闽书》中,亦说是在唐武德年间传入中国的,《闽书》中的记载,谓:
默德那国,有吗喊叭德圣人,生于隋开皇元年,门徒有大贤四人,唐武德中来朝,遂传教中国。一贤传教于广州,二贤传教于扬州,三贤、四贤传教于泉州。
中国回教徒的著作中,有一本小册子,叫《西来宗谱》。在这本小册子里面,文词虽然鄙俚,但书中所叙述的事实,也是根据历来的传说而加以润饰的。在这本小册子里面,说回回传入中国,实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年(西纪628年)。传入中国的原因,是因为太宗梦见妖物窜入宫中,被一缠头者降伏。太宗问于群臣,群臣说缠头者乃西域回回,天方圣王名穆罕默德。太宗乃命石堂赍表到西域去,请穆罕默德到中国来。
穆罕默德不肯来,乃派了三个苏哈爸到中国来,一个叫盖思,一个叫吴哀思,一个叫万个思。盖思和吴哀思,行至嘉裕关,因不服水土病故,只有万个思一个人,随石堂到了中国。后来万个思又修表回国,请选无牵挂者八百余人,来中国帮同传教。回兵到中国后,太宗命在学习巷内建筑一大礼拜寺,给回兵居住。到了唐明皇时,安禄山反,西域回王又选派三千雄师来中国平服安史之乱。此三千回兵,后来就为皇帝的亲兵,并在中国择配。后复分调各省,于是中国各处,皆有回兵。
根据以上各节记载,有的说是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的,有的说是唐朝武德年间传入中国的,有的说是贞观年间传入中国的。而这些记载,皆是见于明以后的记载中,明以前的则无有,是否可靠,颇有疑问。近人的著述中,也多是根据这些记载,并且在各种记载中,皆谓第一个来华传教的人是旺各师(或万个思、干葛思、干歌士、宛噶斯,皆为Sahed Sead Wakkas的译音)。Wakkas究竟是什么人,天方正学旺各师大人墓志中谓:
大人道号旺各师,天方人也,西方至圣之母舅也。奉使护送天经而来,于唐贞观六年,行抵长安。唐太宗见其为人耿介,讲经论道,有实学也。再三留驻长安,因勅建大清真寺,迎使率随从居之。
大人著名讲章经典,劝化各国。嗣后生齿日繁,太宗后勅江宁、广州,亦建清真寺分驻。厥后大人期颐之年,由粤乘船,放洋西去。既抵青石,伏思奉命而往,未曾奉命而还,何可厥梓里,是以复旋粤海。大人在船中复命归真,真体大发真香,墓于广州城外。
在《西来宗谱》附录中的记载,更比较详细些。说先贤挽个士奉命来中国,曾请假回国三次:第一次是回国取经典,传授中原教生;第二次请《古啰呢》(即《天地经》)授徒诵念,并求圣人指示其无常的地方。圣人手指东方,令人用箭向前射去,乃对挽个士说:“凭有我的感应,箭落之处,即汝归结之处,汝且速返中原,后当有验。”挽个士遂登船,随风漂泊,不觉已至粤东,得箭于北垣外流花桥的北头,始悟贵圣感应,明示此处即为他葬身的地方。他就在这个地方,四面砌了一座围墙,又建了一座怀圣寺,并奉旨给土田,为寺内当业,名曰“回回田”。寺内又建光塔一座,高十六丈有奇。塔顶竖立金鸡,随风旋转。每逢七日,上竖大旗,使人知此日是礼拜。
至第三次回国,是挽个士夜梦一高人告诉他,说“贵圣不日辞世,汝可速回西城,面见圣容,迟则恐无及矣。”
挽个士醒后,即束装返国,赶到默底那,而圣人已死。得知圣人有遗言,教他仍回中国传道。挽个士复回到粤东,不久即死,葬在围墙内,“门外颜曰先贤古墓”。
这些传说,是否可靠,则无法证明。据Issar Mason说:穆罕默德的母舅,本名Abuf Wakkas,谓其曾离阿拉伯,又无明文记载。其子叫Saad Ibn Wakkas,亦有呼为Saad Ibn Malik Ibn Wahbay Zuabri的。他是拥护回教的第七人,且曾随穆罕默德氏转战各地,没于亚却(Alig)。时当西纪六七五年(唐高宗上元二年),享年七十九岁,葬于麦加。其一生足迹未涉中国,故野史中所谓圣使,实非其人。
日人桑原隲藏氏也说旺各师传说,是出于附会,并谓在替而生(Thiersant)的中国之回教中,不卢好而(Broomhall)的《中国伊斯兰》中,戴威略(Deveria)的《中国回教起源考》等书中,皆认为是无稽之谈。
Issar Mason根据Abu Zaid al Hafar的游记所载,认为第一个来华传教的阿拉伯人,不是Saad Wakkas,而是伟伯(Ibn Wahab),并且认为传说中旺各师,就是伟伯。广州的古墓,就是伟伯的葬身处。他以为伟伯在以前大概是一个著名的回教徒,阿拉伯游客Abu Zaid,见之于广州时,已为一年高望重之人。他乃是Hebar的遗裔,Al Azud之子科赖士族人,且确与穆罕默德氏有亲戚关系。
伟伯在西安谒见皇帝之后,曾回到伊拉克(Irak),后来复又回到中国。世人不察,竟以伟伯得事迹,张冠李带,而饰为Saad Wakkas的神话了惟Issar Mason之说,亦不无令人怀疑之处。Saad Wakkes来华,各种传说皆谓其在唐初,而伟伯则于唐末来华,在时间上竟相差二百余年。在此二百余年中,回教徒的势力,已日益千里的向外发展,回教徒的足迹,已早到了中国。因黄巢屠杀广州各国异教徒十二万人时,就有许多回教徒在内。这个时候距离伟伯来华的时间,相差无几,可见中国早就有许多回教徒了。并且在西纪八五一年(唐宣宗大中五年)阿拉伯商人苏莱曼(Sulagman)曾作一篇游记,较之Abu Zaid的游记,还早二十余年。在苏莱曼的游记中,记述当时广州的情形如下:
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麕集者,曰康府(Khanfu即广州)。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,教堂一所。……各地回教商贾,既多聚于广州,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,依回教风俗,治理回民。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,朗读先圣戒训。终讲时,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。判官为人正直,听讼公平,一切皆能依可兰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。故依拉克商人来此方者,皆颂声载道也。……中国至是时,仍无一人信回教者。
在这一段记录中,更可证明在伟伯之前,中国早就有了回教徒,早就有了教堂和传教的牧师(与现在的阿訇一样)。牧师的任务,不但管理教务,并且兼管商务。由此看见,传说中的Saad Wekkas的事迹,未必就是伟伯的事迹。
西纪一七八八年(清同治十一年),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拍雷狄斯(Arachimandrite Paladius)曾获得古代汉文大字布告一张,乃是由阿拉伯文译成汉文的。此布告叙述回教初入中国的事迹谓:
唐贞观六年(西纪六三二年)穆罕默德之母舅,依宾哈姆撒(Ibn Hamsan),率徒众三千人,携《可兰圣经》来至中国。哈姆撒道高品善,太宗皇帝见之大悦,并其徒众悉优礼之,留之长安,为筑清真寺一所以居之。嗣后乃于江宁、广州别筑分寺。哈姆撒次与众讨论经义,立规戒,以便遵守。分僧侣为三级,以利传道:第一级曰亦姆妈(Imam);次曰喀梯巴(Khatiba);三曰麦爱清(Mn ezzin)。
“亦姆妈”犹之佛寺之方丈,“喀梯巴”乃讲经者,“麦爱清”则招呼祈祷者。僧之职在讲解圣经,俾众遵守,乱律者惩罚之。布告次又胪列规戒十四条,作信徒之指南:
1.订婚及嫁娶之礼;
2.信徒死时之礼;
3.处置死者方法;
4.送葬之礼;
5.回教徒死后,须诵《可兰圣经》,并须施惠于寡妇及孤儿;
6.回教信女出嫁异教者,罪最重。其叛教之罪,等于叛兵临阵逃亡,虽斩首亦不足以赎罪;即后代子子孙孙,皆有罪孽。媒介人及家长之罪亦等此;
7.须行善去恶,天堂判日,地上苦狱,皆距离不远,上帝赏正罚邪,无能漏网;
8.禁吸烟酒,烟能伤肺,酒能杀身故也;
9.禁止娼妓及赌博。娼妓最为无耻及可厌之人,赌博能伤人道德,使人堕落;
10.禁止放重利债,君子不可损人以利己也;
11.视贫富等级,定征宗教及慈善事业税。贫困极者,免之,用善言劝勉之,俾可自救;
12.奖励设学校,以阐明宗教玄秘;
13.规定祭祀之礼,以便遵行;
14.僧侣须时时记忆本人之天职,教堂寺宇有毁坏者,须慷慨解囊,捐金助修。
此布告中的传说,与《西来宗谱》中的传说,除人名不同外,余均相似。此布告是何时公布的,不得而知。惟依照十四条之规戒看来,也当在明代以后,盖在第八条中谓“禁吸烟酒,烟能伤肺……”我们知道烟草只有几百年的历史。烟草,西方人叫为Tobacco,在哥伦布(Columbus)发现美洲之后,方传至欧洲。在明朝的时候,方由葡萄牙等国商人,传至中国。由此可知,此布告定为明以后的产物,是毫无疑问的。因之,所谓依宾哈姆撒来华传教的事,是否可靠,亦不敢断定。
陈垣氏谓,欲知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,应先知中回历法之不同,回历纪元,明以来皆谓始于隋开皇十九年巳未(西纪599年),其误因洪武十七年(西纪1384年)甲子采用回历时,为回历七八六年,由此按中历上推七八六年,故有此说。若按回历上推七八六年,则实为唐武德五年壬午(西纪622年),与开皇巳未说,相差至二十三年。此二十三年,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一大症结。《西来宗谱》中谓始于唐贞观二年(西纪628年)亦由于误算年数,非有意作伪。所谓贞观二年者,实永徽二年(西纪651年)。贞观二年与永徽二年,适差二十三年,其说本不谬,特误算耳。据此,则回教之传入中国,确始于永徽二年了,惟亦有令人怀疑之处:
第一、《唐书》及《册府元龟》中,皆谓大食于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,也就是阿拉伯与中国正式通使节始于永徽二年。阿拉伯使者之来中国,也许是为着政治上的关系,也许是为着经济上的关系,不一定就是为着宗教上的关系。而且在《唐书》及《册府元龟》中,并无一字说到关于传教的事;
第二、永徽二年,为西纪六五一年,正是穆罕默德氏之后第三任克利弗俄特曼(Othman)时代。此时,回教的势力,已因着阿拉伯的远征队向外伸展,波斯、叙利亚、美索不达米亚、巴比仑、埃及等,已在回教势力统治之下。在东北方面,则与中国的边境相接。回教势力的发展,一方面是由于兵力,一方面是由于海上的商队。在唐初的时候,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贸易,以波斯为最盛,其次则为阿拉伯。且西纪六四二年(唐贞观十六年)波斯全境皆为阿拉伯回教徒所占领。则波斯人之改宗回教,也是必然的事。
因此,在永徽二年以前,必有大批的回教徒——阿拉伯与波斯等国人——来中国经商贸易,同时将他们的宗教传入中国。在陆路方面,回教徒的商队,亦不亚于海上。唐太宗统一葱岭以西诸国,阿拉伯与中国陆路交通的路线,亦随之打通,则回教商队之来中国西北部者,亦必很多;同时亦可将他们的宗教,传入中国。
第三、中回历法,诚然不同。若谓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,各种记载的不同,是由于推算的错误所致,则中国历法,至元、明两代,多采用回历。在元、明两代中,很多有学问回教徒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,来到中国,中国历法改治,他们的功劳颇大。他们既能为中国改治历法,则他们也定会明了回历与中历之不同。假使在他们没有来到中国之前,推算上的错误,也或许难免;但在他们来到中国之后,似不应该再有推算上的错误。且彼时回教在中国历法界中有很大的威权,即便推算错误,他们又为什么不加以纠正呢?
那末,回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?记载虽多,但都是明以后的著作,明以前的则少有见到,故要找出一个确实的时期,是很困难的;惟回教之传入中国,与阿拉伯商人,却有莫大关系,我们只能从这关系中,去寻出其渊源来。
阿拉伯与中国通商,远在隋唐之前就有了,最初的交通,大半是由于陆路,在张骞通西域时,中国就知道有阿拉伯了。惟那时则叫条支(Tajik或Tagi的译音)。陆路通商的路线,是经过中亚细亚,越葱岭,而至中国的京城。后因海上交通日渐进步,乃多舍陆路而取海路。海路交通的路线,是自波斯湾,经过印度,绕马来半岛而至中国的广州,或岭南交州、福建的泉州、浙江的杭州,与江苏的扬州等处。至八世纪以后,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,已完全操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了。
穆罕默德氏之统一阿拉伯,是在西纪六二九年(唐贞观三年)。他统一阿拉伯之后,阿拉伯的人民,自然都改奉了回教。在西纪六二九年之前来华的阿拉伯商人,或者还有一部份是非回教徒;但在西纪六二九年之后来华的阿拉伯商人,可以说完全是回教徒,并且在西纪六四二年(回教徒完全占领波斯)之后来华的波斯商人,也大都是回教徒。
这班经商的回教徒来到中国之后,有的是数年一度的回到本国去,有的是竟长久的居留在中国。他们同教的人,渐渐的多起来,自然会有举行宗教仪式的集合处(即礼拜寺),自然会有执掌教务的牧师,故我们认为回教是在西纪六二九年前后,由于阿拉伯商人传到中国来的。
至于最初来华传教的人,是否为Saad Wakkas,或为依宾哈姆撒,因年久失传,已无可考。至于他的一生事迹,是否如传说中所说,曾往返阿拉伯数次,他每次回到阿拉伯的任务,是为朝觐、取经,及报告旅居中国的教民状况,同时,是否还负有其他政治上及商业上的任务,亦不必深究。
二、回教最初是从海道传入中国的,抑由陆路
回教既于西纪六二九年前后,由于阿拉伯的商人传入中国,则最初是由海道传入的呢,抑由陆路传入的呢?按以上各种记载看来,有谓最初是由陆路传入的,有谓最初是由海路传入的,惟穆罕默德氏统一阿拉伯之前,回教的势力,还未能向外发展;阿拉伯征服中亚细亚,是七世纪末与八世纪初(唐玄宗开元年间前后),最早亦在穆罕默德氏之后。第二任克利弗俄马(Oman)时代(西纪634~644年),在东北方面方能与中国的领土相接。盖在此时期之前,中国对西北各民族,时常用兵,战争是年年发生的,因之,中国与阿拉伯的通商路线,不免有许多障碍,或完全断绝,也是可能的事。
及唐太宗征服中亚细亚各国,阿拉伯商队之来中国西北部贸易,方能通行无阻。如在唐太宗未征服中亚细亚各国之前,阿拉伯的商队,是很难到中国来的;而当时海上交通,日益发展,到了唐朝的时候,波斯人在海上的势力,已被阿拉伯人取而代之。阿拉伯商人之来华,已舍陆路而取海路了。在中国西北陆路未通(因战事及其他障碍)之前,阿拉伯的商队,亦必随波斯商队,从海上而来中国。因之,回教之传入中国,最初实乃始于海路而来,先到中国的广东,因商业的关系,再以广东为根据地而传播至中国的内地;即由广东而至福建,由福建而至浙江,由浙江而至江苏,由江苏而山东,由山东而东三省以及内地各省。
至于陆路传入的时期,则较海路为迟,须至中国的武力已发展到葱岭以西(唐贞观年间),或阿拉伯征服波斯及中亚细亚各国之后(唐开元前后),方能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新疆及西北各处。
中国西北各省的回教徒,大都是从陆路传入的;东南及沿海各省的回教徒,大都是从海路传入的,惟从陆路传入,虽迟于海路,但其势力的发展,则较海路迅速,此除商业上的关系以外,尚有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关系。
唐时借阿拉伯的军队,以平安史之乱(西纪757年),与元人入主中华,皆为其主要原因;并且在西纪八世纪初,当阿密亚(Omeyyades)王朝时代,有许多十叶派(Seyyds)的信徒和阿里(Aly)的后裔,因逃避阿密亚王朝的压迫,乃逃到呼罗珊(Chorassan)。但阿密亚王朝对他们搜索颇严,他们为避免敌人陷害计,又逃到中国,所以回教在陆路方面的发展迅速,其原因颇多;而海路方面,只有商业上的关系,故其势力的发展,当然远逊于陆路了。
回教虽然在西纪六二九年前后传入中国,惟此时的中国回教徒,可以说完全是阿拉伯人,或其他外国商人,而中国人信仰的则很少,也可以说是没有。因回教在中国不传教,且因地理环境、物质生活,与风俗习惯等的不同,更因中国人固有儒道与佛理的信仰,故很难得到中国人再信回教;就是到现在,汉人之改信回教的,除因特殊的原因外,仍然很少。
这般阿拉伯商人,有的是久居中国而不返的,日久,自然会与中国人发生婚姻上的关系。唐时,外人与汉人发生婚姻关系的已很多,如唐贞元三年四千胡人归化的事,许多西域使者,都在长安娶妻买田,不愿归国。所谓西域,当然包括阿拉伯、波斯,及中亚细亚各国在内,其中一定也有许多回教徒在内。此指长安一地而言,在中国其他通商大埠中,回教徒的人数,或比长安多至若干倍。如肃宗时田神功兵掠扬州,大食、波斯胡贾死者即有数千人;又黄巢陷广州,外国的回教徒,及其他异教徒,竟有十二万人被屠杀。这许多久居中国的回教徒,娶中国女子为妻,定是常有的事。
中国人的宗教信心并不深,且唐初对于各种宗教,皆取放任主义,故中国女子,既嫁给回教徒为妻,当然会被丈夫所同化,而改信回教。中国人之信奉回教,也就是从这种关系开始。安史之乱,两京沦陷,肃宗曾借阿拉伯兵以收复两京。这些阿拉伯兵,或同西域,回纥等国一样,因讨逆有功,就有一部份留在中国,而与中国妇女结婚,后竟永久的居于中国。到了元人入主中华,回教徒在中国的势力,愈加发展,全国各地,到处都有回教徒的足迹了。
三、中国的回教寺始于何时,以何处为最早
至于回教徒在中国所建的礼拜寺,究竟是始于何时,以何处为最早?长安的清真寺,照碑文看来,是始于天宝元年(西纪742年),但此碑极不可靠,乃明人所伪托,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;且在Abu zaid的游记中,记当时伟伯在长安,并未曾见过长安有回教徒的礼拜寺,可见长安之有礼拜寺,定是以后的事。
日人足立喜六氏在其所著《长安史迹考》中说:创建清真寺碑,据桑原博士考证,系明代伪作,不信其为唐物;而此碑观在昔唐皇城内司农寺处,自非当时建立清真寺的所在地。唐时,大食人以通商为目的,至中国南方之广州以及其他各港从事贸易,而长安、洛阳等内地,亦有其踪迹;但当时阿拉伯商人,并无集团的奠居内地,故无建寺尊教之必要。
清初毕沅(秋帆)著《关中胜迹图志》,对关中胜迹,引证颇详;惟在寺观条中,对于长安清真寺的记载,仅寥寥数语:
清真寺在长安东北,(通志)明洪武十七年,尚书铁玄修;永乐十一年,太监郑和重修。
对于寺中碑文,也只字未提。假使王鉷的清真寺碑是天宝元年所立,较之大秦景教碑(西纪七八〇年)还早三十余年,则其价值当在景教碑之上;但中国历年的学者,对此碑并未加以注意,亦可见其为后人所伪托而无疑。因之,长安的清真寺建于天宝元年之说,也是不可靠的。
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有两个最古的回教寺,一个是现在广州的怀圣寺,一个是建在福建晋江县(即泉州)的清净寺。泉州亦为古代蕃商荟集的地方,唐时就有阿拉伯商人至此贸易。此地早就有了回教寺,当然是可能的事。
耳奈司(Arnaiz)与卜谦(Max Van Bershem)两氏,在不久以前,曾公布清净寺的阿拉伯字碑文于世,碑为回历七一〇年(西纪1310~1311年,元武宗至大三年至四年)所立。碑文中载此寺建于回历四百年,为中国最早的回教寺。回历四百年,乃西纪一〇〇九年——一〇一〇年,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——三年。但元时吴鉴的《清净寺记》中则谓:“宋绍兴元年,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,自撒那威(Sisaf)从商舶来泉,创兹寺于泉州南城,造银灯香炉以供天,买土田房屋以给众。”绍兴元年,为西纪一一三一年,与阿拉伯文碑中所载,又相差百余年;可见此寺创于何时,已异说纷纭了。
阿拉伯文碑中谓此寺是回教徒在中国所建最早的回教寺,但并不尽然,在苏莱曼《东游记》中,说他在广州的时候,就见到有回教的教堂了。他的游记是成于西纪八五一年,即唐宣宗大中五年,可见唐朝的时候,广州早就有了回教寺了;泉州的清净寺,并不能算是回教徒在中国所建最早的回教寺。不过苏莱曼在广州所见到的回教寺,是否就是现在的怀圣寺,虽然是一个疑问,但中国的回教寺最初建立于广州,是不可否认的。
广州的怀圣寺,据许多记载中,皆说是唐时所建;寺中尚有一塔,叫作怀圣塔。此寺于元至正十年(西纪1350年)重修,其碑文中记:
白云之麓,坡山之隈,有浮图焉,其制则西域磔然石立,中州所未睹。世传自李唐迄今,蜗施蚁陟,左右九转,南北其局,其肤则混然,若不可级而登也。其中为二道,上出为一户,古碑□漫,而莫之或纪……
清仇池石《羊城古钞》中记寺与塔的情形,谓:
怀圣寺在广州府城西二里,唐时番人所创,内建番塔,轮囷凡十有六丈五尺,广人呼为光塔……相传塔顶旧有金鸡,随风南北。每岁五六月,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,呼号以祈风信,不设佛像,惟书金字为号,以礼拜焉。
桑原骘藏氏以为怀圣寺及番塔(即怀圣塔)在唐人著作中,绝无记载。其最古的记载,则见于南宋方信孺之《南海百咏》中,其文中谓:
番塔始于唐时,曰怀圣塔,轮囷直上,凡六百五十丈(恐有错误),绝无等级,其颖标一金鸡,随风南北,每岁五六月,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,叫佛号,以祈风信,下有礼拜堂。
桑原氏谓此记载,颇为怀疑,他以为怀圣塔或非唐时所建,而与岳珂《桯史》中所记蒲家窣堵波之构造样式,及其顶上之金鸡,恐非偶合;所以他疑为怀圣塔或者就是蒲家窣堵波之遗物,怀圣寺或即宋代蒲寿庚的先人所建。
桑原此说,亦不过是推测之词,并无确实证据,岳珂《桯史》中所记蒲姓窣堵波的情形如下:
……后有窣堵波,高入云表,式度不比他塔,环以甓为大址,累而增之,外圜加以灰饰,望之如银笔。下有一门,拾级以上,由其中而圜转焉,如螺旋,外不复见,其梯每数十级启一窦,岁四五月,舶将来,群獠入于塔,出于窦,啁嘶号呼,以祈南风,亦辄有验。绝顶有金鸡甚巨,以代相轮,今亡其一足……
此与《南海百咏》中所记,颇相类似,若此塔果为蒲姓遗物,则定为宋时所建,而非建于唐时,但有数点令人怀疑之处:
第一,关于窣堵波的记载,只见于岳珂之《桯史》中,在宋代其他著作中,则少有记载;
第二,在《桯史》中,岳珂明明白白的说:“绍兴壬子(西纪1192年)先君帅广,余甫十岁,尝游焉。今尚识其故处,层楼杰观,晁荡绵亘,不能悉举焉。然稍异而可纪者,亦不一,因录之以示传奇。”则岳珂此记,还是根据他十岁时在广州所见闻者。但在他十岁的时候所见所闻,如有错误,是否能加以判断?在他再赴广州时,对幼年时所见者,是否尚能完全记忆而无遗忘?
第三,《桯史》中并谓:“有堂焉以祀名……堂中有碑,高袤数十丈,上皆刻异书,如篆籀,是为像主。”则此堂是回教徒的礼拜寺,是毫无疑问的。蒲姓的住宅,或在寺之附近,或在寺的范围以内,亦未可知。由此看来,怀圣塔就是蒲姓的窣堵波,总不免令人怀疑。又若谓怀圣寺为蒲寿庚的先人所建,更令人不敢相信。
我们若从塔的作用上来看,则怀圣塔与其说是为着宗教,还不如说是为着商业。因商业较之宗教,还要重要的多。广州是外商麇集的地方,在从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道门户,外国的商船,第一步总是先到广州。而中国的商舶,亦多由此放洋,其在商业上的重要,可想而知,《萍州可谈》中记:
船舶去以十一月、十二月,就北风;来以五月、六月,就南风。船方正若木斛,非风不能动……
前节所述:“每岁五、六月,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,呼号以祈风信。”乃完全是为着商业上的作用。怀圣塔叫作番塔,广人又呼为光塔,阿拉伯人夜间行祈祷时,祈祷呼报人(Muazzin)携灯而登;塔外远眺,有如灯台。如此,则与现在各海岸所用的灯塔何异?塔上有金鸡,随风南北,则与现在所用指示风向的风信器,又有何异。
每岁四、五月,南风起的时候,他们皆于五鼓携灯登绝顶,当然是为着船舶入港的便利而设,所谓叫佛号,以祈风信,最大的作用,也还是在祈祷上帝,保佑他们的商船平安入港,不致迷失途径,与发生其他危险。宗教的作用,乃是因此而附带发生的。
我们知道,唐时回教徒的商队,主要的多是从海路而来,因事实上的需要,为着他们商船的安全与商务的发展,自然会有像现在灯塔与风信器等的建筑。因之,怀圣塔建于唐时,并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商业上的作用,与宗教上的作用,二者是不可分离的,故在他们到了广州之后,即建寺与建塔;一方面为着商业,一方面为着宗教,也是必然的事。
若谓怀圣寺与塔建于宋时,则未免太迟了;而苏莱曼《东游记》中,则明明记当时的广州,已有了回教寺了。他所记的回教寺,或者就是现在的怀圣寺,亦未可知。总之,为着商业上的关系,与宗教上的关系,在唐朝的时候,广州已有了回教寺,而且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回教寺,是毫无疑义的。
本章的结论如下:
第一、回教是在西纪六二九年(唐太宗贞观三年)前后,因商业的关系,传入中国;
第二、最初来华传教的人,因年久失传,已无可考;
第三、因海上交通的日渐发展,回教最初是从海道传入中国的;
第四、因回教商人久居中国,与中国人发生婚姻上的关系,方有中国人之改奉回教;
第五、中国的回教寺,也因为商业上的关系,最早是建立于广州,此寺或即现在的怀圣寺。

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