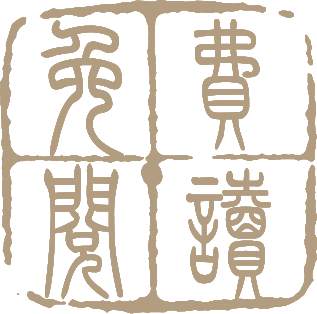
|第四章|
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
回教的发展,是阿拉伯商业资本主义的结果。此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后,当时回教商人之来中国经商者,亦不亚于现代的西洋人;致在政治上、经济上,常常发生很密切的关系。同时因为回教武力的发展,及中国历代之经营西域,乃发生了直接的接触。自回纥族改信回教以后,回教徒与中国的关系,更复杂了。兹就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,分别叙述如下:
一、回教徒在唐代
有唐一代,回教徒与中国政治上、经济上各方面的关系,也就很复杂了。唐时,回教徒之来中国者,多聚居于广州、交州、泉州、扬州,及长安等处。在这些通商大埠中,他们的人数确是很多,如在肃宗上元元年(西纪760年)宋州刺史刘展反,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出兵讨之。兵至扬州,曾大掠居人,发冢墓,大食、波斯贾胡死者,即有数千人。又黄巢攻陷广州后,外国的异教徒,被屠者竟有十二万之多;并且因为黄巢之乱,对外贸易完全停顿,而海外万里的西拉甫(Siraf)及瓮蛮(Oman)两地人民以及完全是依赖与中国经商为生的,至此时,均失业破产,可见在经济上的关系,是何等密切了。
回教徒之来中国分海、陆两路。唐初回教徒之来中国经商者,多从海路;至陆路方面,除经商者外,还有一种移民的性质。当阿拉伯阿密亚王朝时代,有许多十素派的信徒及阿里(Ali)的后裔,因不堪阿密亚王朝的压迫,皆逃至中国境内,后来竟永久的居留在中国境内了。
旅居中国的回教徒人数日渐增多,自然的会与中国人发生婚姻,及其他一切的世俗关系,如《资治通鉴》中记:
初,河西、陇右既没于吐蕃,自天宝以来,安西、北庭奏事及西域使在长安者,归路既绝,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……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,或四十余年,皆有妻子,买田宅,举质取利,安居不欲归;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,凡得四千人……胡客皆诣政府诉之,泌曰……岂有外国朝贡者十余年不听归乎?今当假道于回纥,或自海道,各遣归国。有不愿者当于鸿胪自陈,授以职位,给俸禄,为唐臣……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,泌皆分隶神策两军。王子、使者,为散兵马使或押牙,余皆为卒……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,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。
这些胡客,既然是西域各国的使臣,并且欲假道于回纥,或自海道遣归,当然有许多回教徒在内。他们有妻子,有田宅,并且还有治生之道——举质取利。其与中国人的关系,可想而知。他们既长久的居住于中国,则受中国人所同化,也是必然的事,甚至攻读中国的儒书,以考取科第。在唐宣宗时,即有回教徒李彦昇考取进士的事,《全唐文》陈黯《华心》篇中纪李彦昇登进士第谓:
大中初年(西纪八四七年)大梁连帅范阳公(即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卢钧)即大食国人李彦昇属于阙下。天子诏春司考其才,二年,以进士第名显,然常所宾供者不得拟……
唐代进士很难考取,盖须通五经、明时务,且登第之后,亦最为荣誉,往往有读书终生,须发尽白,尚不能及第。李彦昇竟以一回教徒而登进士第,其对中国学问研究之深,可想而知。
李彦昇的名字也是华名,必另有一亚伯拉的名字,因欲在中国考取科第,不得不改用华名;或是他的祖先居留中国日久,早就改从华姓与华名了,此在宋元之时期更多。
在唐代除李彦昇以外,回教徒读中国书应试及第者颇多,惟其姓名传后世者甚少,如钱易《南部新书》中记:
大中以来,礼部放榜,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,亦谓曰榜花。
所谓色目人,即塞外人,乃西域人的总称。色目人中定有许多回教徒在内,是无疑的。
唐代回教徒与中国政治关系,亦颇复杂,亚拉伯与中国正式通使节是始于永徽二年(西纪651年),自此以后,亚拉伯使臣来中国朝贡者,史籍中记载颇多。
唐初亚拉伯统一内部之后,即向外发展,首当其冲者,则为波斯。波斯为亚拉伯所败,波斯伊嗣侯曾于贞观二十一年(西纪647年),遣使至中国求援,唐太宗给波斯王的诏书中说:
国君相救,理固然矣!然朕自贵大使之口,得闻亚拉伯族为何等人,其风俗习惯,其信仰宗教,其首领之品格,皆甚详尽。人民如斯之忠信,首领如斯之才能,焉有不胜之理乎?尔其慎修德谨行,以博彼等之欢也。
康国为亚拉伯所侵略,亦来中国称臣求援,太宗曰:“朕恶取虚名,害百姓,且康臣我,缓急当属同其忧,师行万里,宁朕志耶!欲不受。”
以唐初贞观之盛,对此新兴的回教国家,亦不敢用兵;想唐太宗对于亚拉伯的情形,必然是深知洞悉,故不敢妄动干戈。
至西纪八世纪初,亚拉伯又侵略葱岭以西诸国,伊拉克总督哈嘉智遣屈底波及摩哈美德、依实喀锡姆二将进征中国,于西纪七一五~七一七年(唐玄宗开元三年至五年)葱岭以东的喀什葛尔,亦被屈底波所攻陷。葱岭以西的康国、安国、俱密国,吐火罗等国,皆于贞观年间,为中国的蕃属;因被亚拉伯人所侵略,不堪压迫与虐待,俱上表请中国援助,以驱逐亚拉伯人的势力。
《册府元龟》中所载开元年间,安国、康国求援的表文如下:
七年(西纪719年)二月安国王笃隆波提遣使上表论事曰……自有安国以来,臣种类相继作王不绝,并军民等亦赤心奉国,从此以来,彼大食贼,每年侵扰,国土不宁,伏乞天恩滋泽,救臣苦难,仍请勅下突厥施令救臣等。臣即统领本国兵马,计会翻破大食,伏乞天恩,依臣所请……
同年(开元七年)同月,俱密国与康国,亦皆有同样的求救表文。至开元十五年(西纪727年)吐火罗国亦上表求援,其表文中谓:
吐火罗叶获遣使上言曰:奴身罪逆不孝,慈父身被大食统押,应彻天聪,颂奉天可汗进旨云,大食欺侵我,即与你气力;奴身今被大食重税,欺苦实深,若不得天可汗救活,奴身自活不得,国土必遭破散,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!伏望天可汗慈悯,与奴身多少气力,使得活路……
在开元二十九年(西纪741年),石国王伊吐屯屈勒亦遣使上表求援,谓:
奴自千代以来,于国忠赤,只如突厥骑施可汗,忠赤之中,部落安贴;后背天可汗,垂底大起,今突厥已属于天可汗,在于西头为患,惟有大食,莫踰突厥。伏乞不弃突厥部落,讨得大食,诸国自然安贴。
可是唐朝在开元年间,已不若贞观时之强盛,故对这些求援诸属国,皆无实力的援助,仅慰遣来使而已。
中国军队与亚拉伯军队的直接接触,是在大宝十年(西纪751年)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讨石国,斩其王车鼻施,西域诸国不服,乃乞兵于亚拉伯,攻恒暹斯域。高仙芝军大败,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中记:
天宝初,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,赐铁券。久之,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,请讨之。王约降,仙芝遣使护送至开远门,俘以献,斩阙下,于是西域皆怨,王子走大食乞兵,攻恒暹斯域,败仙芝军,自是臣大食……
《旧唐书·李嗣业传》亦记:
初仙芝给石国王约为和好,乃将兵袭破之,杀其老弱,虏其丁壮,取金宝瑟瑟驼马等。国人哭号,因掠石国王,东献之于阙下,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。群胡忿之,与大食连谋,将欲攻四镇。仙芝惧,领兵二万深入胡地,与大食战。仙芝大败。会夜,两军解,仙芝众为大食所杀,存者不过数千……
在此役中,中国人被亚拉伯掳去者甚多,杜环即为俘虏之一。他居亚拉伯十余年,于肃宗宝应初年(西纪762年)方得随商船由海路归广州。他曾将他在亚拉伯的所见所闻,写了一篇《经行记》。在此记中,谓与他们同时在亚拉伯的,尚有汉匠作画者京兆人樊淑、刘泚,织络者河东人乐环、吕礼。可见在此役中,中国人之被俘虏者必然很多。
玄宗末年,安禄山叛,两京沦陷,代宗曾借西域各国兵士收复两京,亚拉伯亦皆出兵中国,帮助中国勘定安史之乱,《册府元龟》中记:
至德二年(西纪757年)九月,元帅广平王领朔方,安西、回纥、大食兵十五万,将收西京……十二月贼军大溃,余军入城中,嚣声辄夜不止。癸卯,元帅广平王整军容入长安,中军兵马使濮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、大食等,从城南过浐水东下营。
由此可见回教徒在唐代,与中国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关系,是何等的密切与繁复了。
二、回教徒在宋代
回教徒与中国商业上的关系,至唐而渐盛,至宋乃登峰造极,因宋代对海外贸易颇加奖励,如《宋史》中记:
雍熙中(西纪984~987年)遣内侍八人赍勅书金帛,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。
其奖励的方法,甚至有以官爵授与外商者,如:
绍兴六年(西纪1136年)知泉州连南夫奏请,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,抽解物货。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,补官有差,大食蕃官啰辛贩乳香,值三十万缗,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,收息钱九十八万缗,各补承信郎,闽、广舶务盐官抽买乳香,每及百万两转一官。
宋代之所以要奖励贸易,是在增加税收,以充国用,如:
绍兴七年(西纪1137年)上谕:市舶之利最厚,若措置合宜,所得动以百万计,岂不胜取之于民,朕所以留意于此,庶几可以宽民力耳。
绍兴十六年(西纪1146年)上谕:市舶之利,颇助国用,宜循旧法,以招徕远人,阜通货贿。
宋代既奖励外商来中国贸易,则外商(包括诸回教国商人)之来中国者,较之唐时,必更多若干倍。每年十月外商返国之时,中国官府,皆须设宴为之送别,如《岭外代答》中记:
岁十月,提举市舶司,大犒蕃商而遣之。
《桯史》中亦记:
常因犒设,蕃人大集。
这也是奖励外商来华贸易的方法之一,因当时财政困难,市舶之利,乃是国家的重要收入,不得不有种种奖励的方法。尤其是在南渡以后,国家财政更是要依赖海税收入来维持。海税收入之大,动以百万计,不但现在如此,在以前亦复如此,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中记:
海舶岁入,象犀、珠宝、香药之类,皇佑中五十三万有奇。治平中增十万,中兴岁入二百余万缗。
两浙、闽、广三市舶司,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。
海舶收入既如此丰,则主其事者,必定会有中饱舞弊及刮掠外商等事发生,如《乾隆泉州府志》中记:
先是海商货至,官竞刮取,命曰和买,实不给一缗,于是商舶滋少,供贡缺绝。
据亚拉伯商人所传,呼罗珊(Khorssan)商胡,在广东与官市使争市价,怒其强买,曾亲往长安,告其不法。中国官吏的刮掠,外商多裹足不前,一时海外贸易大减,而国家的岁收亦骤形减少。为恢复国家财源之收入计,乃有宁宗开禧三年(西纪1207年)取缔刮掠外商的禁令。
……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,其余货物,不得毫发拘留,巧作名色,违法抑买,如违许蕃商越诉,犯者计脏坐罪。
海外贸易既盛,则中国钱币亦流至海外各国,为各国所通用。但当时海外各国输入中国者,多以香药、珠玉、象牙、犀角为主;而中国输出者,则以金、银、铜钱、绢、瓷器等为主,致中国的金、银、铜钱,如现在的白银一样,源源流至外国,在国内乃发生钱荒,《郡国利病书》中记:
南渡以后,经费困乏,一切倚办海舶,岁入固不少,然金、银、铜、锡、钱币亦用以漏泄外境,而钱之泄尤甚。
元丰以后(西纪1078年),公私上下,并告乏钱,百货不通,人情窘迫,谓之钱荒。……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,令敕具载,而自熙宁七年,颁行新敕,删去旧条,以此边关重车而出,海舶饱载而回,闻治边州军钱出外界,但每贯征收税钱而已。钱本中国宝货,今乃与四夷共用……又置市舶于浙、于闽、于广,舶商在来,钱宝所由以泄,是以自哈安门以下江海,皆有禁……
钱荒的情形,竟至“百货不通,人情窘迫”,其严重可想而知。中国钱币的外流,在唐代也就有了,当时也曾禁止出口。至宋代因海外贸易繁盛,流出更多,后虽加以禁止,惟“禁令虽严,然奸巧愈密,其弊卒不可言”。至愈弄愈穷,甚至影响于国家之大局。
宋初,回教商人及其他外商居留中国者,皆聚居于一处,如《萍州可谈》中记:
广州蕃坊,海外诸国人聚居,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,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,蕃官为之,巾袍履笏如华人……饮食与华同,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式,受戒勿食猪肉,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。又曰:汝必欲食,当自杀自食,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。至今蕃人,非手刃六畜则不食,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……
到了后来,则渐与中国人杂居,如《桯史》中记:
番禺有海僚杂居,其最豪者蒲姓……岁益久,定居城中。
此在宋人著作中记载颇多,当时回教徒及其他外国商人的豪富,并不亚于现在海上的洋商,《岭外代答》中记:
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,莫若大食国。
《桯史》中记亚拉伯商人蒲姓的豪富,谓:
其挥金如粪土,舆皂无遗,珠玑香次,狼籍坐上,帷人曰:此其常也。
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亦记:
宋时蕃商巨富,服饰皆金珠罗绮,器用皆金银器皿。
顾氏书中又引苏辙《龙川略志》所记辛押陁罗之豪富,谓:
蕃商辛押陁罗者,居广州数十年矣,家资数百万缗。
辛押陁罗即为亚拉伯的回教商人,《宋史·外国传》大食条中,并记其欲助修广州城事,谓:
熙宁中,其使辛押陁罗乞统察蕃长专司公事,诏广州裁度,又进银钱助修广州城,不许。
辛押陁罗请求助修广州城虽未许,但在宁宗嘉定四年(西纪1211年)泉州城的修筑,则由外商——回教徒出资修理,明阳思谦《泉州府志》中记:
嘉定四年,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,请于朝而大修之,城始固。
藤田博士并宋南宋林湜为泉州晋江县时,得泉州诸蕃之助,造沿海警备战舰,亦可见当时外商之富力及与中国之关系了。
唐代,外商在中国即享有一部份的治外法权,到了宋代亦复如此,《萍州可谈》中记:
蕃人有罪诣在广州鞫实,送蕃坊行遣……徒以上罪,则广州决断。
在《宋史》中,关于处置外人犯罪的记载颇多,《张朂之传》中有:
夷人有犯,其酋长得自治,而多惨酷,请一以权法从事。
《王涣之传》中有:
蕃客杀奴,市舶使据旧比,止送其长杖答,涣之不可,论如法。
《汪大猷传》中有:
故事,蕃商与人争斗,非伤折罪皆以牛犊,大猷曰: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,苟在吾境当用吾法。
这里所谓蕃商,实回教徒居其多数,盖当时代海上贸易之权,完全为回教徒所独占。
回教徒与中国人通婚之事,到了宋时亦更多,《萍州可谈》中记:
元祐间,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,官至左班殿直,刘死,宗女无子,其家争分财产,遣人挝登闻鼓,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,因禁止,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。
可见宋时对于中外通婚之事,并无限制。宋会要绍兴七年(西纪1137年):
大商蒲亚里者,既至广州,有右武大夫曾讷,利其财,以妹嫁之,亚里因留不归。
想当时如曾讷这样的人,亦并不在少数,而回教徒的妇女,嫁与中国人为妻妾者亦多,如《萍州可谈》中又记:
乐府有菩萨蛮,不知何物,在广州见呼蕃妇为菩萨蛮,因识之。
菩萨蛮乃“Bussurman”的译音,而Bussurman又由Mussulman而来,其字源出于亚拉伯语Muslin,《元史》作“木速鲁蛮”,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作“铺速满”,《北使记》作“没速鲁蛮”,皆是此字的异记。
宋代,回教徒在中国读书应试者,较唐时更多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记:
海獠多蒲姓及海姓,渐与华人结姻,或取科第。
所谓海獠,乃是自海上来华通商之南蛮人的总称,回教徒居其多数,其姓‘蒲’者,必为回教徒无疑。在《宋史·大食传》中,亚拉伯的贡使,多为“蒲”姓,如开宝九年(西纪976年)的蒲希密,太平兴国二年(西纪978年)的蒲思那,至道元年(西纪995年)的蒲押陁黎,景德元年(西纪1004年)的蒲加心,天禧三年(西纪1019年)的蒲麻勿陁婆离,嘉祐中(西纪1056~1603年)的蒲沙乙等皆是“蒲”姓,是由Abu的读音而来;而亚拉伯的人名之前,多加Abu一字。中国读其音为“阿蒲”,后省其“阿”,则视为“蒲”姓了。
宋时各地所设立学校,亦皆允许外人子弟入学,如龚明之《吴中纪闻》中纪程孟师熙宁间(西纪1068~1077年)和广州政绩谓:
……大修学校,日引诸生讲解,负笈而来者相踵,诸番子弟皆愿入学。
宋代,不但各地所设立的学校,允许外人入学,并且还有专门为外人设立的学校,以教育外人,如蔡绦铁《围山丛谈》中记:
大观政和之间(西纪1107~1117年)天下大治,四夷响风,广州、泉州请建番学。
这些番人中,当然大部份是回教徒,盖自西纪八世纪至十五世纪,在此数百年间,中国对西方的海上贸易,完全操之于回教徒手中;而亚拉伯武力所及之处,多改奉回教,故当时来中国经商者,可以说完全是回教徒。
宋末蒲寿庚、蒲寿岁兄弟,均曾为中国官吏,蒲寿岁知梅州有惠政,并且还善作诗,有《蒲心泉学诗稿》,可见宋时回教徒读书应试及研究中国学问者必甚多。
自唐代以来,回教徒之居留中国北方者即多,在唐代则以国都长安为中心,在宋代则以国都开封为中心。宋室南迁之时,北方大乱,居于中国京城的回教徒,亦皆随宋至而迁至江南,《西湖游览志》中记:
先是宋室徙跸,西域夷入安插中原者,多从驾而南……
又志余中记:
锁懋坚,西域人,其先扈宋而南渡,遂为杭人。
在中国的回教商人,不但豪富,而其势力亦颇强大,如蒲寿庚、蒲寿岁兄弟居泉州时,南海一带,海贼猖獗,后袭泉州。寿庚与寿岁曾帮助中国官府,击退海贼。后元人攻陷临安(杭州),景炎地至闽(西纪1276年,即至元十三年),授蒲寿庚以福建广东招讨副使之职,兼统闽、广海舶,即希望寿庚援助,以恢复已失的江山;但蒲寿庚知宋室大势已去,并未为宋室尽力。
后来宋室因船舶军资,皆感不足,于是在泉州强征寿庚的海舶与资产。寿庚大怒,乃投降于元;而景炎帝不得不离闽赴粤,宋室天下,至此亦无恢复的希望。在景炎帝二年(西纪1277年,即至元十四年)七月,张世杰乘元军离闽之时,曾急攻蒲寿庚于泉州。当时泉州为南宋外宗正司所在地,宋宗室居于此者有数千人,欲响应张军,皆被蒲寿庚所屠杀。
后蒲寿庚又为元人招致海南各国,故极得元人所优遇,因之蒲姓子孙在闽的势力颇大,泉人避其薰炎者八十余年。直至元亡之后,蒲姓在闽的势力方衰。
在北方,辽金与亚拉伯之贡使往来,《辽史》中曾记与亚拉伯联姻事:
开泰九年冬十一月壬寅,大食国进象及方物,为子册割请婚。太平元年三月,大食王复遣使请婚,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。
后耶律大石西迁至中亚细亚,契丹人、女真人(即元时称之曰汉人),随之西去者亦多,如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记邪米斯干城(即撒马尔罕)的情形谓:
城中常十余万户,国破而来者,存者四之一,其中大多回纥人(泛指回教徒而言),田园不能自主,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(即西夏人)等,其官长亦诸色人为之,汉人工匠,杂处城中。
回教著作家依宾爱儿阿梯儿(Ibnel Athir)记西辽征服土耳其斯坦的情形如下:
西纪一一二八年(宋高宗建炎二年),秦国(Sin即中国)葛尔罕(Garkhzar)号“跛者”(即耶律大石),率领大军至喀什噶尔边境,喀什噶尔阿合马(Abmed)……兵败而死。葛儿罕抵土耳其斯坦时,见境内已有本国人甚多。葛尔罕至,秦人皆通款降附,葛尔罕因之得征服土耳其斯坦全境。
葛尔罕后率兵征马瓦拉痕那儿(Maeramabar),其地君长为马莫德(Mahmud),摩哈美德之子也……西纪一一三七年勒墨藏月,两军持战,马莫德军败,遁归撒马儿罕传檄全国,又遣使……檄所有回教徒,集合全力,以抗异。……奉回教诸国,皆遣军来援……西纪一一四二年两军大战,回教徒之军大溃……自是以后,契丹人及突厥人立国于马瓦拉痕那儿,葛尔罕卒于一一四三年,其女嗣位,不久即卒,葛尔罕妻嗣位,后乃传之其子摩哈美德(Mobammed)。
按摩哈美德,回教徒极普通的名字,耶律大石之子亦用此名,想亦改奉回教,且在《辽史》中谓大石死后,“子幼,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,……在位十四年”,普速完亦类似回教的名字,大概因西辽的百姓都是回教徒,为便于统治起见,或者也改奉回教了。
西辽既建国于土耳其斯坦,则其与报达哈里伐政府的关系,当亦更密切了。
三、回教徒在元代
元代崛起于蒙古,武力最盛,蒙古人铁蹄所到的地方,皆要受其蹂躏与屠杀,西亚回教各国人民遭其屠杀者,动以万计。本来成吉思汗在征服西辽旧地以后,并不预备西征,曾修书于花剌子模,请保界通商,花剌子模王也答应了。后来成吉思汗派了四百多人(都是畏兀人)随同西域商人到西域去购买货物,花剌子模人说是蒙古的奸细,尽数杀掉,只逃脱一个人,跑回去报告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大怒,乃起兵攻打西亚诸回教国家,因此,西亚诸回国,乃被蒙古人所灭。
亚拉伯到了西纪十世纪以后,非常衰落,又回到回教未兴以前的獉狉状态。元宪宗三年(西纪1253年)旭烈兀率郭侃西征,只几年的工夫,亚拉伯就被元人所征服了。《元史》中纪征服报达时的情形如下:
……至报达,西戎大国……侃兵至,破其兵力七万,屠西域,又破东域……城破,哈里伐算滩……乃自缚,诣军门降,其将纣答尔遁去,侃追之……获纣答尔斩之,拔三百余城,又西行三千里,至天房……巴尔算滩降,下其城一百八十五。
又刘郁《常德西使记》中亦记:
七年(西纪1257年)丁巳岁,取报达国……王师至城下,一交战,破胜兵四十余万。西域既陷,尽屠其民,寻围东城,六日而破,死者以数十万,哈里伐以舸走,获焉。
回教徒之遭元屠杀,其惨状可见一般。
元人在征服西亚诸国以后,方转兵东征,扫灭中原。在东征的军队中,各族人都有,回教徒尤占多数。
宋室偏安汴南,其势虽敌不过元人,但宋室善水战,而元人所统率的军队,是西北各民族混合组成的,只知陆战,不谙水战,所以要消灭宋室,也要费相当的力量与时间;然而元人却利用蒲寿庚、蒲寿岁兄弟的力量,将宋室消灭了。蒲寿庚当时曾总管东南沿海一带海舶,海上势力颇大,所以能消灭宋室;而蒲寿庚之降元,不但与宋元势力的消长大有关系,且一方面可以利用蒲寿庚在海上的势力,以镇压东南沿海一带的反元势力;一方还利用他以招致南海诸国臣服于元,如《元史·董文炳传》中说:
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,寿庚素在市舶,谓宜重其权,使为我扦海寇,诱诸蛮臣服,因解所佩金虎,符佩寿庚矣!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,帝大嘉之。
蒲寿庚之见重于元,可想而知,所以有元一代,蒲姓在闽的势力颇大,泉人避其薰炎者八十余年。
回教徒随元军来中国的,或经商来中国的,皆久居中国不返,故周密说:
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,江南尤多。
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亦谓:
元时,回回遍天下。及是,居甘肃者尚多。
据Cderic说,当时居于杭州的回教徒,占全市民人口二十分之一,约四十万家,这或者有点儿言过其实,但亦可知当时居于杭州的回教徒是很多。
先是,宋室徙跸,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,多从驾而南。元时内附者,又往往编管江浙、闽、广之间,而杭州尤夥,号色目种,隆准深眸,不啖豕肉,婚姻丧葬不与中国通,诵经持斋,归于清真。
在《至顺镇江志》中载,当时镇江的人口是三千八百四十五户,而回回即有五十九户,一万零五百五十口中,即有回回三百七十四口,二千九百四十八驱(孑身无家之人)中,即有回回三百一十驱。在罗哥孛罗游记中,亦皆谓中国各地莫不有回教徒的足迹。
元代,回教徒来中国贸易者亦多,如《至正集》所录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中记:
西域大贾擅水陆利,天下名城区邑,必居其津要,专其膏腴。
可见回教商人,在中国通都大邑经商者,也不亚于现代的西洋人。且元初于平定江南之后,也曾努力恢复海外贸易,如至元十八年(西纪一八二一年)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,蒲寿庚等曰:
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,皆有慕义之心,可因蕃舶商人,宣布朕意,诚能来朝,朕将宠礼之,其往来互市,各从所愿。
《元史·食货志》亦有:
至元十四年,立市舶司一于泉州,令忙古解领之,立市舶司三于庆元、上海、澉浦,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,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;及次年回帆,依例抽解,然后听其货卖。
于是南海诸国如占城、马八儿等回教国家,皆先后来中国贸易,也渐渐恢复宋时海外贸易的盛况。
回教徒在元代入住于中国者更多,因为元统一欧亚,回教徒随元人来中国者,多至不可以胜计,故在中国做官者亦多,如王礼所说:
惟我皇元,肇基龙朔,创业垂统之际,西域与有劳焉,洎于世祖皇帝,四海为家,声教所被,无此彼界,朔南名利之相往来,适千里者如在户庭,之万里者如出邻家,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,学于南夏,乐江湖忘乡国者众矣,岁久家成,日暮途远……一视同仁,未有盛于今日也。
王氏所言,诚非虚语。
元代分人民为四种,一为蒙古人,二为色目人,三为汉人,四为南人。所谓色目人,即指属于蒙古人之西域各民族的人民而言;汉人即以前的金人,是指居于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国人而言;南人即宋室遗民,是指居于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的中国人而言。色目因有功于元,故极受元人的优遇。
元代自延祐初年(西纪1314年)举行科举,色目人每次登进士第者,辄有数十人,至少也有十余人,中间虽经废除,然举行者犹有十五六科,故色目人之“仕于中朝,学于南夏”者实在很多。且蒙古人之征服中国,因色目人之功劳颇大,故色目人之待遇,也与蒙古人同,而汉人与南人则望尘莫及,如《元史》中记:
各道廉访使,必择蒙古人为使。或缺,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。
在《元史》中,关于此种记载颇多,到处都可以发现。当时的重要官职,除蒙古人外,即以色目人为最得势。在元世祖建元以后,所任命的丞相中,非蒙古者只有十六人;而此十六人中,色目人即占其十二。
所谓色目,乃是当时公牍中所用的名称,在普通的著述中,多用“西域”二字。西域各国葱岭以西的,可以说是完全信奉回教;葱岭以东的,亦有许多已改奉了回教,故在色目人中,回教徒亦不在少数。
元代回教徒的闻人颇多,在《元史》中有专传者,约数十余人。今列举如下:
扎八儿火(《元史》卷一二〇)、曷思麦里(《元史》卷一二〇)、阿剌瓦而思(《元史》卷一二三)、赛典赤赡思丁(《元史》卷一二五)、纳速剌丁(同上赡思丁子)、忽辛(同上赡思丁子)、怯烈(《元史》卷一三三)、爱薛(《元史》卷一三四)、撤吉思(同上)、察罕(《元史》卷一三七)、彻里帖木儿(《元史》卷一四二)、赡忠(《元史》卷一九〇)、纳速剌丁(《元史》卷一九四)、迭里线宝(《元史》卷一九六)、阿老瓦丁(《元史》卷二〇三)、亦思马因(同上)、阿合马(《元史》卷二〇五)
在《新元史》中尚有:
牙剌洼赤(《新元史》卷一三三)、哈贝哈心(《新元史》卷一三一)、库尔古司(《新元史》卷一五〇)、也速(黑)迭儿(《新元史》卷一五一)、乌马儿(《新元史》卷一五五)、倒剌沙(《新元史》卷二〇四)、弈赫抵雅尔丁(《新元史》卷二一四)、获独步丁(《新元史》卷二三三)、穆鲁丁(同上)、海鲁丁(同上)、萨祁剌(《新元史》卷二三八)、丁鹤年(同上)
此外在元史中无传者尚有:
乌巴都那。福扎剌鲁丁,父亲福的哈鲁丁,并封吉国公,宰相表大德十一年,乌巴都那参知政事。
赡思丁。一作苦思丁,集贤大学士,提纲回回司天台事,子布八,元统二年为秘书卿。
雅老五实。燕京大断事管,子阿里伯,一作阿里别,行省宰相表至元十三年,阿里伯以江淮平章政事行省于怀东,十七年十二月坐法死,后谥忠杰。
马合麻。姓不花剌氏,洪城屯卫百户,子撒的迷失,孙阿合麻,并赠咸阳郡公,曾孙买述丁,中政院使海道万户府达鲁花赤。(见《朱德润集》。)
哈八兀。以丁为氏,祖迷儿阿里,父勘马剌丁,子慕马,元统年进士。(见《癸酉进士录》。)
乌马儿。回回阿里马里人,曾祖阿撒,祖本八儿沙,父阿思兰沙。(见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)
阿都剌。回回黄马里人,曾祖丁答木丁,祖阿里,父酒不丁。(见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)
穆古必文。回回氏,曾祖沙的,祖祈都,父捏古伯。(见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)
剌马丹。回回氏,曾祖伯八剌黑,祖马合谋,父哈里丁。(同上。)
剌马丹。于阗氏,亦回回人,祖兀尔别,父迷的阿里,剌马丹字勘马拉丁,以字行,为广海盐课司提举,子二,沙不剌丁,次哈八赤,佥浙(西辽察司事)。
耶尔脱忽。回回古速鲁氏(按“古”或为“木”字之误,即木速鲁蛮。(见《危素集》,又作回纥。)
别罗沙。西域别朱八里人氏,曾祖木瓦剌,祖别鲁沙,父苦思丁,其母回回氏,其妻答失蛮氏,亦回回人。
节显儿的。木速蛮氏,大德十一年官祕书少监。(见《祕书志》。)
脱颕。木速鲁蛮氏,曾祖远哥,祖囊加台,父教化的。(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)
木八剌吉。回回人,至元六年祕书卿。(见《祕书志》。)
也速兀兰。阿鲁混氏,亦称阿尔浑氏,亦称阿拉温氏,领天下诸匠弓矢炮手(按即回回炮手总称)。
哈散。阿鲁温氏,礼部尚书,宰相表皇庆元年平章政事,阿散升左丞相,延祐七年四月罢。
理熙。阿鲁温氏,至元四年祕书典簿。(《祕书志》。)
达理于实。阿鲁温氏,字寿之,至元二年怯里马赤。(《祕书志》。)
伯笃鲁丁。答失蛮人,字至道,至元元年官祕书太监。(见《祕书志》及元时选王逢称为鲁至道。)
哲马鲁丁。回回人。(见《元诗选》。)
别里沙。回回人,字彦诚,见《元诗选》,与别罗沙异。
亦都忽立。别吉林公,后改信佛教。
高克恭。字意敬,号房山,其先西域人,后居燕京,官刑部尚书。(见苏天爵《元文类》,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。)
买闾。西域人。祖哈只,家上庆,父亦不剌金。买闾,字兼善,嘉兴儒家教授(见《王逢集》)。
马九皋。回纥人,以字行,弟九霄。(见杨朝英《太平乐府》及陶宗仪《书史会要补选》。)此回纥即回回。
丁野夫。回纥人。(见《图绘宝鉴》。)
木撒肃。崇仁县达鲁花赤。(见吴澄《文正集》,按:《辍耕录》木楔非为回回人小名。)
溥博。西域阿鲁温人,曾祖哲立里,祖道吾,父剌哲。溥博本名道剌沙,字仲渊,嘉兴教谕。(见宋濂《銮坡集》。
萨德弥实。田江郡侯,有《瑞竹堂经验方》。(见吴澄《文正集》。)
合剌甫丁。系本合撒尼,父可利马丁,子木人剌沙,哈马丁,阿老天丁,忽赛因。(见《两浙金石志》。)
阿老丁。回回大师建真教寺。(见《西湖游览志》、《杭州府志》。)
吉雅谟丁。字元德,丁鹤年兄,有诗名。
爱理沙。丁鹤年兄,字允中,有诗名。
优机沙。有诗名。
荣僧。字子仁,回纥人,登进士第,官至江浙行枢密经历。
马某沙。回回人,泰定元年知枢密院事及御史大夫。
伯帖木儿。回回人,武宗至元年间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鲁坤。赡思祖父,太宗时,以材授其定济南等路榷课税使。
益福的哈鲁丁。祖名扎剌鲁丁,父名乌巴都剌,子名乌巴都剌,翰林院回回国子学教授。
以上诸人,有的是在中国建功立业的,有的是立言立行,为一代师表的。元人入主中华不及百年,回教徒的闻人竟有如此之多,此不但在中国史上为空前的纪录,即在世界史中,各国亦无此先例。
但以上所举,仍不免挂一漏万。因元代的著作中及史籍中,关于各人的氏系及所属何教,总是含混笼统,分辨不清。有的一概名之曰西域的,有的一概名之曰色目的,有的一概名之曰回纥的,或回鹘的,有的名之曰回回的,有的名之曰畏吾或伟兀的,有的名之曰阿鲁浑的,有的名之曰答失蛮的。在当时的习俗,对回教徒虽多称之为回回,但在公牍或文人的著作中,多改回回为回纥,或改为西域,或改为色目,使后人无从分辨,致前所举者仍不能尽详。
在上列诸人中,最奇者是赛典赤赡思丁父子、丁鹤年、赡思诸人。《元史·赛典赤赡思丁传》中谓:
(至元十一年)拜平章政事,行省云南……云南俗无礼仪,男女往往自相配偶,亲死则火之,不为丧。祭无秔稻桑麻,子弟不知读书,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,婚姻行媒,死则为棺槨奠基;教民播种,为陂池以防水旱;创建孔子庙、明伦堂,讲经史,授学田,由是文风稍兴……西南诸夷,翕然款附……制衣冠袜履,易其卉服草履,酋皆感悦。赛典赤居云南六年,至元十六年卒,年六十九岁,百姓巷哭,葬鄯阐北门……
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个回教徒,他在太祖西征的时候,才投降于元。但他入仕中国之后,竟以中国的礼俗去教化云南人及西南诸夷,并且还建孔子庙、明伦堂,讲经史,完全以儒家的办法,去教化云南人,使云南由野蛮而变为文明。这总是空前少有的事。
回教徒是最反对跪拜与棺椁祭奠的,但赛典赤赡思丁到了云南以后,不但不反对,且大加提倡。他的治理云南,一切皆采用中国的礼俗,可见他对于中国文化,是何等的崇拜了;而他本人受中国文化的陶冶,又何等深切了。
赡思丁有五个儿子,第三个儿子叫忽辛,颇有父风。赡思丁在云南所置的学田,后来都被僧徒占去,经忽辛力争,又从僧徒手中追回,并令郡邑遍立庙学,选文学之士为教官。因之,云南的文风大兴。像这样的事,就是以一个中国人来做,也就够令人钦佩的了,何况入仕中国不久的回教徒——赡思丁父子竟做出这样轰轰烈烈的事来,实在是十古难得的。
丁鹤年也是一个回教徒,他到中国亦不久。他的父亲叫职马录丁,他的哥哥,一个叫吉雅谟丁,字元德;一个叫爱理沙,字允中,皆有诗名。丁鹤年不但诗作得好,文章也写得好,日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三经,也是一个儒学。家此外,他对于算数、导引、方药等事,也皆有深切的研究。但他晚年却笃信佛教,这也是一件极大的奇事。回教徒的信仰绝坚,但丁鹤年的信仰,却由回教而转到儒教,又由儒教而转到佛教,一再变迁;这在回教徒中,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的。
丁鹤年晚年笃信佛教,主要的原因,或者是受着环境的影响。因他正生在元明交替的时代,不得不如此以保全他的名节与生命;惟他对于父母的丧葬,皆采用中国的习俗,而抛弃其本来的习俗了。戴良《高士传》中记:
鹤年父武昌公死时,鹤年年甫十二,已屹然如成人。其俗素短丧,鹤年以为非古训,乃服斩三年;及夫人捐馆舍,鹤年哀毁尽癯,盐酪不入口者五年。
乌斯道《丁孝子传》中说:
鹤年避地二十余年,兵后还武昌,访生母葬地,自秋至冬,偏询莫知者。鹤年作母主,早暮拜母主前,求五旬有报。拜至七日夜,梦母氏出高堂中,以恸即寤。晨起,邻老杨重者至云:吾昨夜梦子之母氏,堂宇间自内出,以酒肉见赐。鹤年以梦母与邻老同,试即其地物色之,见平陆土有降下者,意谓吾闻母葬时无棺椁,上覆败舟板,人与板腐尽乃尔。遂陈酒肉以祭。祭罢,断其土,骨果见,然恐他墓偶有同者,复啮指血骨上,良久抆去,血骨通变茜色,乃将骨棺敛葬是乡,鹤年卢墓终身。一时论者,咸称为孝子。
服斩三年,此乃中国古制,拜母主、酒肉陈祭、血骨棺敛等,也是中国的习俗,而非回教的习俗。元代回教徒受华化之深,于此可见一斑。
丁鹤年有姊名月娥,寇陷武昌时,抱其女与诸妇女一同投江而死,后父老以“十节同志死,不可异圹,乃作巨穴,同葬焉,题其名曰十节墓。其弟鹤年,相与树碑墓下,以昭节行。”《明史·烈女传》中亦有传。月娥颇有才学,丁鹤年幼时读书,皆月娥所口授。
赡思字得之,是元好问的再传弟子。他不但对于中国经史各书的根基很深,就是关于天文、地理、水利、律数等学问,亦皆有深切的研究,并有许多著述。他一生有著作十余种,文集三十卷,惜皆失传,仅存《重订河防通议》一书。他的为人颇耿直,多言人所不敢言,行人所不敢行的事,《元史》中记其一生事迹谓:
……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,见帝于龙虎台,眷遇优渥。时倒那沙柄国,西域人多附焉。赡思独不往见,倒那沙屡使招致之,即以养亲辞归。天历三年,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,赐封奎章阁……诏预修《经世大典》,以议论不合求去……至正四年,除国子学博士,丁内艰不赴。后至元二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,即上封事十条,曰法祖宗,揽权纲,敦宗室,礼旧勋,惜名器,开言路,复科举,罢数军,一刑章,宽禁锢。是奸臣变乱成患,帝方虚已以听。赡思所言,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。
……四年,改签浙东肃政廉访司事,以病免归。赡思历官台宪,所至以理冤泽物为己任。平反大辟之狱,先后甚众。
……至正十年,召为袐书少监,议治河事,皆辞疾不赴。十一年,卒于家,年四十有七。
……赡思邃于经,而尤精于易。至于天文、地理、钟律、算术、水利、旁及外国之书,皆究极之。家贫,饘粥或不继,其考定经传,常自乐也。所著述有《四书阙疑》、《五经思问》、《奇偶阴阳消息图》、《老庄精诣》、《镇阳风土记》、《读东阳志》《重订河防通议》、《西国图经》、《西域异人传》、《金哀宗记》、《正大诸臣列传》、《审听要诀》,及文集三十卷,藏于家。
赡思虽生于中国,他的祖父鲁坤,最初入仕于中国,想对于中国文字,定还不大认识;只数十年的工夫,他在中国竟成为一个有名的儒学家。对于中国四书五经研究得这样深切,著作这样的丰富,学问这样的渊博,不但在中国回教徒中要数第一,就是同中国历代的儒者比较起来,亦毫无逊色。
元代中国的回教徒,除赡思、丁鹤年外,以诗文名,以书画名者颇多。据陈垣氏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一文,统计元代中国的回教徒:
儒学家有赡思丁、忽辛、赡思溥博。
佛老家有丁鹤年、亦都忽立。
文家有赡思。
曲家有马九皋。
诗人有萨都剌、丁鹤年、吉雅谟丁、爱理沙、鲁至道、哲马鲁丁、仇机沙、别里沙、买闾。
书家有萨都剌、荣僧、马九皋。
画家有高克恭、丁野夫。
建筑工程家有也黑迭儿、马合马沙父子。
元代中国回教徒之有著作者:
蒲寿晟,《心泉学诗稿》、《心泉诗余》。
赡思,著作十三种,文集三十卷(见前)。
丁鹤年,《丁鹤年集》、《丁孝子诗集》、《皇元风雅》。
高克恭,《房山集》、《高尚书文集》、《高文简公文集》七卷。
萨都剌,《雁门集》、《萨天锡诗集》二卷、《集外诗》一卷、《萨天锡逸诗》、《西湖十景词》。
察罕,《圣武开天记》、《纪年纂要》、《太宗平金始末》。
萨德弥实,《瑞竹堂经验方》。
扎马鲁丁,万年历。
可里马丁,万年历。
元初,因西域各国皆入版图,故所用文字亦颇复杂。元世祖至元六年(西纪一二六九年)以前,尚无蒙古字,皆以汉文及畏吾儿文为主。到了至元六年,方颁行蒙古文字,凡玺书颁降,皆以蒙古新字为主,仍以各国文字为副。
至元二十六年(西纪一二八九年),因与西域交通频繁,又采用亦思替非(Istakhr)文字,置回回国子学,以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为教授,教授回回语。其毕业生即为各官厅的翻译官。至仁宗延祐元年(西纪一三一四年)四月,复置回回国子监,亦思替非文字,乃波斯文字,回回国子学所教习的文字,则为波斯文。回回文字主要的是用于葱岭以西的三藩国,后中央势力大衰,渐失其统驭能力,回回文字也就很少使用,故“回回学士亦省,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”。
在西北三蕃中,以伊儿汗与回教的关系最为复杂,且与回、耶两教势力的消长,关系亦最大。伊儿汗各王所信仰的宗教如下:
旭烈兀,太祖之孙,破报达,回回教,礼耶教。
阿八哈,旭烈兀子,曾以兵击埃及回教王比拔尔斯,以辅助十字军。
阿鲁浑,阿八哈子,崇耶教,黜回教。
台古塔儿,阿八哈弟,幼曾受耶教洗礼,名尼古拉斯,后改崇回教。
盖喀图,阿鲁浑之弟,奉回教。
贝杜,盖喀图从弟,奉回教。
合赞阿鲁浑之弟,改奉回教,仍优礼耶教。
合尓班答,合赞弟,幼受耶教洗礼,亦名尼古拉斯,后改奉回教。
不赛因,合尓班答子,奉回教。
观此,耶教虽曾得势一时,但其势力,终敌不过回教,故最后回教仍占优势;而蒙古民族,至最后亦皆改奉回教了。蒙古民族改奉回教的最大原因,是在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,因其所属的人民,盖全是回教徒,与他教绝不相容,故在政治上,回教各国虽为蒙古人所征服,但在精神上,回教却征服了蒙古人。
四、回教徒在明代
明初,回教徒之建功立业,而为国家所重任者,甚多。如开国元勋常遇春,为中国改治历法的的马沙亦黑(又名吴谅),三保太监下西洋的郑和诸人,对于明室的功绩,也并不小。有明一代,中国回教徒的闻人亦颇多。兹据《清真释疑补辑》中所录,略述如下:
常遇春,江南怀远人,初从刘聚,薄其掳掠,乃借私卒数十归太祖。采石之役以后,颇得信任,与傅友德时号二虎将。寻守溧阳,攻建业,克陈友谅,抚张士诚。洪武元年(西纪1368年),奉命北定中原,破济南,克汴梁,复同徐达合兵,取长芦,克通州,入元都,不戮一人,封府库,吏民安堵,封鄂国公。二年(西纪1369年)下保定、中山、真定,会徐达克太原,山西悉平。七月病卒于军中,追封开平王,谥忠武,赐葬钟山。其子常茂,自少随父居戎幕,参军务,洪武四年(西纪1371年)封为郑国公。
沐英,字文英,江南定远人。八岁遭兵乱,父母没,太祖抚养之,履从征讨有功。洪武十一年(西纪1378年),讨吐蕃、川、藏。十二年平洮州十八族番酋之叛。十三年与傅友德出征云南,破元军,而诸蛮亦皆望风来附,云南悉平。英留镇云南,垦地凿池,通盐井,利商族。二十五年(西纪1392年)卒,谥昭靖,追封黔宁王,子沐春、沐晟、沐昂。
沐春有父风,袭封平西侯,嗣镇云南,善抚士卒,与下同甘苦。洪武二十八年(西纪1395年)越州蛮酋叛,春与都督何福之,共同讨之。三十年破缅蛮,三十一年(西纪1398年)八月卒。
沐晟,袭侯封。永乐三年(西纪1406年),八百大甸酋叛,晟讨平之。四年,讨安南;五年,安南平,封为黔国公。六年讨交趾之乱,后留镇云南,抚绥夷人,恩礼有加,远近化服。
沐昂,洪武十八年(西纪1385年)平缅有功,留镇云南。昂雅性素谦,喜与文士交,卒谥武襄。其子璘,喜读书攻诗,后以都督镇云南,轻财好客,守祖父成规,抚治有方,故夷人皆畏威衔德。
海源善,洪武初为湖广安化县令,甫下车,即倡修文庙,课絃诵,文风丕振。性宽慈,视民如子。仿天方国制,以熟皮为鞭,民有小过,但扑之使知愧而已,因之境内大治,狱无系囚。
铁铉,字鼎石,河南邓州人,由国子生升山东参政,后为山东布征参赞军务。寻进兵部尚书,反抗成祖,故于成祖即位后被擒,触成祖之怒而被杀。(按铉有二女,于铉被杀后发教坊司,女誓不受辱。已而放出,各上诗一律谢恩。其长女诗中有“旧曲听来犹有恨,故园归去已无家。”之句,曾传诵一时。)
平安,回纥人,洪武末,帅守定州。建文三年(西纪1401年)与吴杰拒燕兵,屡败成祖,後闻天下已为成祖所得,遂饮鸩而死。
沙玉,永乐初为河南涉县令,清俭爱民,深得人民信仰。
沙坤瑞,江西余干人。性孝,十六岁丧父,家贫无资,典身以殓。种蔬养母,四时鲜味无缺。母殁负土成坟,庐墓三年,未尝见齿。
沙金,陕西延安人。嘉靖中(西纪1522~1566年)任威茂参事,节法严明,军容为诸边冠,威镇一方,人号沙家军。性朴素,素食布衣,有儒者风。
回谦,江南巢县人,以博雅称一时。宣德中(西纪1426~1435年)任监察御史,后擢庆元府太守,不数年而化行德普,歌颂不衰。
?茂,湖广公安县人,少颖悟,无书不读,下笔数千言,书法尤超妙。性清朴,登天顺甲申科(西纪1464年)进士。廷试时,帝不识其姓,后改为陕。
陈大策,正德中(西纪1506~1521年)官北京后军都督府。时武宗留心诸教,尝面访之,陈进天方国经三十卷,翻译详解,帝大悦。
达云,凉州卫人。万历初(西纪1573年)历官甘肃参将,收复松山,拓地五百里。加太子少保,平青海边患,名震西陲。
赛哈智,天方圣裔,雅度优容,动由礼节,有西汉长者风。守经砥行,以教道自任,钦封世袭咸宁侯。
吴谅,原名马沙亦黑,撒马儿国人也。随西使陈诚来中国。太祖深奇之,命制浑天仪,以正前代得失,授为刻漏博士。所著有《法象书》诸篇。帝特设回回博士科,以官其偕来者;并命刘基、吴宗伯译其经。寻授内灵台太史院。永乐三年(西纪1406年)随驾达燕京,授钦天监五官灵台郎,世袭秋官正职。帝每以长者目之。成祖虽盛怒时,辄取矢诚规谏。其子景忠,袭父职,后裔继承家学,终明之世,俱官天文生,世袭罔替。
王岱舆,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人,祖籍天方国。洪武初,其祖入贡金陵,帝召问历法天文,颇能精通,改正从前之谬误,授职钦天监,赐居南京。岱舆世承家学,幼习经文,长读儒书,自六经、《论语》以及周、程、张、朱之学,靡不博习贯通,著《正教真诠》四十篇,刊行于世,为清真教中第一册之汉文著作。
马云衢,字赓宇,云南元江州人。天启间(西纪1621~1227年)官教谕,勤于训课,风俗为之一新。寻选天河县令,颇有廉声,峒番亦皆感服。
以上是根据《清真释疑补辑》中所录,当然也是不完全的。因自元朝以后,回教徒在中国做官的,或在社会中有相当地位的,大都皆讳言自己是回教徒,甚至有出教者。就是到了现在,恐怕也还不免有这种情形。故自元代以后,中国的回教徒,多令人无从分别,至著作中记载亦甚少。
在上录诸人之外,尚有郑和,对明代的功勋颇大。郑和自永乐三年(西纪1406年)至宣德八年(西纪1432年)曾七次奉使下西洋,历三十余国,擒叛王三人,为中国在海外开辟若干殖民地。这在中国历史中,实在是空前的伟举。
现在福建泉州(晋江县)域外回教先贤墓中,尚有《郑和下番路经泉州时行香碑记》。在西安的清真寺中,也有一块碑,碑上载“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重修”,可知郑和也确是一个回教徒,惟郑和虽奉回教,但他的信仰并不坚,也曾改奉过佛教,《佛说摩利支天经》经后永乐元年(西纪1403年)姚广孝题记中云:
今菩萨戒弟子郑和,法名福善,施财命工,刊印流通,其所得胜报,非言可能尽矣。一日怀香过余,请题,故告以此。
郑和下西洋,他的部下亦大多是回教徒,如马欢及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等,也都是回教徒。郑和之所以能建树如此伟大的功绩,与回教的关系颇大。
因为蒲寿庚的降元与屠杀泉州宋赵宗室,以及蒲姓子孙在闽的横暴,故明太祖即位后,即禁止福建蒲姓后裔,不得读书入仕,如《全南杂志》中记:
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子(孙)不得齿于仕,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,故终夷人也。
《日知录》中亦有:
明太祖有天下,诏宋末蒲寿庚、黄万石子孙,不得入仕。
《闽书》中亦有:
皇朝太祖禁蒲姓者,不得读书入仕。
明太祖的禁止蒲姓子孙读书入仕,固然是为着蒲姓的先人有倾宋之罪,但在元末明初时,泉州的回教徒,曾据有泉、兴两府叛乱,前后共十年——起于至正十七年(西纪1357年)春,终于至正二十六年(西纪1366年)五月——兴泉两府的人民,迭遭屠杀,几无噍类。到了洪武元年(西纪1368年)明兵南下,才把泉、兴两府作乱的回民平服。这也是禁止蒲姓子孙读书入仕的一个原因。
阿拉伯的回教人,在西纪七世纪至十世纪是最隆盛的时代,到了十世纪以后,就渐渐的衰落了。但因为过去数百年的基础,仍旧职掌海上贸易的霸权。直至十六世纪,欧洲民族国家兴起,商业向外发展,日益千里,回教徒在海上的霸权,才完全被欧洲人夺去。
回教徒与中国海上贸易的关系,在明初尚有相当的发展,但不久之间,即为葡萄牙人所替代了。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,谓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,可见其在海上的势力,多已丧失了。明代阿拉伯贡使之来中国,也是陆多。所以贡使到中国来,固然也有的是为着政治上的关系,但最大的目的,还是由经济上的关系。如《明史·天方传》中记,所谓“赐赍有加”、“赐币及敕奖其王”、“估其贡物,酬其值”、“按籍给赐,籍所不载,许自行贸易”、“番使多贾人,来辄挟重资,与中国市”等语,皆可证明所谓外番来中国朝贡,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贸易而已。此不但明代如此,以前各代,亦皆如此。外国朝贡,大多是经济上的关系,政治上的关系还在其次。
回教商人来中国贸易,在宋代即常受中国官吏的剥削与敲诈,在明代也常有这种事件发生。明应宗成化二十三年(西纪1486年)阿拉伯回教徒阿立,因其兄纳的在中国四十余年未归,欲来中国云南访寻,乃携带了巨万的宝物,至满剌加,附海舶入京进贡。到了广东,他的宝物即被市舶官韦眷所侵尅,阿立乃到京城去上诉,礼部时估其物,酬其值,允许他至云南访兄。后来韦眷惧罪,乃诬阿立为间谍,说他是假贡行奸,令广东守臣将阿立驱逐出境。阿立受此冤枉,无法伸诉,乃号泣而去。
回教徒对于这班贪官污吏的劫夺,也常常不甘忍受,有时也采取一种报复的办法,如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谓:
番使多贾人,来辄挟重资与中国市。边吏嗜贿,侵刻多端。类取偿于公家,或不当其值,则咆哮不止。是岁,贡使皆黠悍,既习知中国情,且憾边吏之侵尅也,屡诉之,礼官却不问。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,当番使入贡时,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、玉石诸物,使臣憾之。一日遇洪于衢,即执诣官,以证实其事。礼官言事关国体,须有处分,以服远人之心,乃命三法司锦衣卫,及给事中,各遣官一员,赴甘肃按治,洪获罪。
明代对于贡使(即变相的外商)防范颇严,恐怕他们来中国窥伺虚实,为中国边患。故常“严饬边吏,毋避祸目前,贻患后日,食纳款之虚名,忘御边之实策”。中国的闭关政策,自此时已开其端倪了。
当元灭明初之际,元宪驸马帖木儿(帖木儿是娶察合台汗女为妻。元代宗王女婿亦称驸马,故明史称为驸马。)统一中亚细亚,建都于撒马尔罕,称成吉思可汗,以元太祖铁木真自比。帖木儿也是笃信回教的,布哇(L.BouVat)在其所著《帖木尔帝国》中说:
统治全亚细亚,就是帖木儿的梦想。他最急的,是脱离中国的属藩,并使中国归向回教。
所以帖木儿闻听元室被明人光复后,就想兴兵为元复仇。但中国在明太祖的时候,国内统一,天下大治,帖木儿亦未敢妄动,所以表面上仍是时常遣使来中国朝贡,并与中国边关互市。
在洪武二十八年(西纪1395年),太祖亦命兵科给事中傅安及其属官郭骥、御史姚臣、中官刘维等,赍玺书币帛报聘。后成祖践祚,中国国内发生战争,帖木儿乃将傅安等拘留,并派人领导傅安周游国内,以誇耀其国土广大。
永乐二年(西纪1405年),帖木儿乃出兵东征中国。严寒就道,白首亲征,雪深丈余,兵马冻死了颇多。永乐三年(西纪1406年),将假道别失八里,向中国边境进发。忽然身得寒疾,因年已老迈(时,帖木儿年已七十余),不久也就死了。因之,帖木儿征服中国的志愿亦未达成。有人说,假使帖木儿不死,征服了中国,恢复元室,恐怕中国人民,也将完全变为回教徒哩。
帖木儿死后,帖木儿帝国亦分裂。至其孙哈里嗣,乃派人将傅安等送回中国,复来中国朝贡。自此以后,中国亦常派使节报聘,直至万历年间(西纪1573~1619年),仍然朝贡不绝。
至于南洋各岛国,因阿拉伯人及波斯的人往来贸易,有许多国家已改奉回教了。这些回教国家,在明初,与中国的关系亦颇复杂。三保太监七次下西洋,即是至南洋各国发展中国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于海外的。郑和所历各国,其人民大多信奉回教,均来中国称臣朝贡,其关系之密切,亦可想而知了。
五、回教徒在清代
清朝统一中国之后,对种族上的待遇,极不平等。清朝对蒙、藏二族,甚是优待,而极力压迫回、汉人民。汉人是居于彼征服的地位,满人恐怕汉人起来光复,当然要加以压迫;但为什么满人却偏偏优待蒙人、藏人,而对回人也加以压迫呢?大概蒙、藏二族,与汉族的关系很少,同化的程度以很微弱,易于受其利用,故汉族被满人打败后,蒙人、藏人对汉族也并没有什么同情心。至于回人则与汉人的关系很深,在中国境内,到处都有回教徒的足迹,受汉人的同化亦深,故对汉人的失败,回人是表同情的。因为如此,才被满人所忌妒,而加以压迫。
如顺治五年(西纪1648年),甘肃回教徒米剌印、丁国栋等,奉明朝的后裔延长王朱识镕起事,反抗清兵,据甘、凉二州,进据西安,清朝乃命固山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,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率兵讨之。
到了顺治六年(西纪1649年)春,米剌印、丁国栋等方被清军克服。清朝当初也曾想利用回人,如元代之利用色目人一样,来统治汉人,但因为中国的回教人是太多了,又不敢利用。同时又怕回人与汉人联合,所以对回人也加以压迫。回人因不堪满人的压迫,时常起来反抗,故有清一代,自乾隆以至光绪(西纪1783~1908年),前后不过百数十年,而回教徒反抗满清压迫的战争,大小共有十余次之多。此起彼伏,蔓延于新疆、青海、宁夏、甘肃、陕西、云南等省,兹略述如下:
清初分西域(葱岭以东的新疆全部)为两大部:一曰准部,一曰回部。准部即准噶尔,为额鲁特蒙古四部之一,在天山以北一带;回部即土耳其斯坦族,在天山以南一带。回部分黑山派与白山派,白山派普通又叫白帽回回,是穆罕默德族的后裔;黑山派普通又叫黑帽回回,非穆罕默德族的回教徒。两派互相倾轧,白山派首领阿巴克(或作阿蒲),为黑山派首领伊士摩儿(或作伊司买、伊司马哀)所逐,阿巴克乃由克什米尔到西藏去,求救于达赖喇嘛五世。因此,于康熙十七年(西纪1678年),回部乃为准部所并。准部后来侵犯蒙古,康熙曾三次亲征,方将准部平服。
回部为准部并后,白山派首领玛罕木特,又苦于准部的压迫,想据叶尔羌(沙车)自立,碑准酋知道了,把他捕了囚在伊犁,并将他两个儿子:长名布罗尼特,次名霍集占,一同囚在伊犁。布罗尼特与霍集占,就是史家所称的大小和卓木(Khoja意即教长)。
当清兵初入伊犁时,准噶尔想利用他们为后援,就将大和卓木布罗尼特放出,并且借兵给他,教他收复天山南路;小和卓木霍集占则仍被留于伊犁,以统帅天山北部的回教徒。大和卓木不久即将天山南路平定,乾隆二十一年(西纪1756年),清兵再定伊犁,霍集占乃逃出伊犁,与其兄布罗尼特共商独立之事。
清兵平定准部后,曾遣使去招抚回部,但回部鉴于以前为人奴隶,所受种种压迫,知臣属于人,终非长久之计,乃决意独立;于是一面召集族众,举行独立仪式,一面传檄各城,准备和清兵对抗。天山南路的回教徒数十万,皆争起响应;惟库车的回教领袖鄂对,惧怕清兵强盛,乃到伊犁去投降清军。霍集占闻之,即杀了鄂对的亲族,增兵把守库车。
当此时,清将兆惠这副都统阿敏图为回部招抚使,被回人诱获,由是决裂。兆惠乃移兵南征,因为兵少,被回人围困于叶尔羌。富德往救,也被围于呼拉玛。后来清朝援兵大至,围方得解。同时回部内部意见不一,又因赋税繁重,以致渐渐解体;而清兵乃于乾隆二十五年(西纪1760年)六月分兵进攻喀什噶尔及叶尔羌。大小和卓木闻清兵大至,乃弃叶尔羌,同亲族逃到巴达克,被巴达克的回酋所杀。并把他们的首级献给清朝,于是天山南路回部,才被清军平定。
清军平定回部后,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,各大回城亦设办事大臣,以治军事。各大臣皆是满人,又于各城设立若干“阿奇木伯克”(新疆回教徒的大小官职,皆曰“伯克”,最高者为“阿奇木伯克”,统理城镇大小事务),铸“乾隆通宝”钱币一种,与回地旧有的普尔钱并行,并豁免租税,限制汉人与回人来往,婚姻关系亦严厉的禁止。国民非有世职,或官至四品以上者,不准留辫发。
回部因地处边远,又当新附之后,办事大臣,往往藉战胜余威,压迫回民,而伯克等亦与他们狼狈为奸,以故不久,又有乌什之变。乌什伯克霍吉斯,在大小和卓木叛时,即态度不明。清朝恐他反复无常,乃召他入京,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。
阿布都拉部到乌什后,暴戾无亲,鱼肉土著,办事大轮苏成,耽于酒色,不问政务,致乌什回民所受痛苦,无处可诉。适葱岭以西布哈尔、阿富汗诸国,嫉清朝威震西域,恐举兵西征,又恨巴达克山同类相残,乃组织同盟军攻打巴达克山,将巴达克山王杀了。乌什回人闻之,乃遣使乞援。
至乾隆二十九年(西纪1764年)二月,举兵反抗清朝,将苏成阿布都拉及以下官吏守兵,一齐杀尽。阿克苏及库车大臣,先后前往救援,皆被乌什人打败,于是伊犁将军明瑞及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,合兵会剿,而乌什所期望之阿富汗等国同盟军亦未来救援,故不久即为清军所灭。清兵入城后,大事屠杀,丁壮者屠尽,老弱者徙于伊犁,并将参赞大臣移到乌什。
乌什变后二年,又有昌吉之变,未几亦被平复。
在甘肃的回教徒分新、旧两派,旧派奉经习默诵,有循化厅的回教徒名叫马明心,从海外归来,见西域回经皆朗诵,遂创立新教,反对旧派的默诵,于是两派相互仇杀。至乾隆四十六年(西纪1781年)三月,马明心的徒弟苏四十三,联合新派教徒数千人,杀死旧派教徒百余人,并将兰州知府杨士机及河州协副将新桂也杀了。兰州总督勒尔锦乃调各镇兵马会剿,将新派首领马明心捕获。新派回教徒二千余人,乃攻陷河州,围困兰州,要求释放马明心。布政使王廷赞使马登城谕众,后来又把他杀了,于是更引起新派回民的愤怒,清廷乃派大学士阿桂出兵,与旧派回民合力征剿,历战三月余,方将新派教徒剿灭。
新教徒被剿后,清朝官吏,以查办新派余党为名,恣意骚扰,又激起回民之反抗。伏羌县阿浑、田五等,乃聚集新派教徒,于乾隆四十六年(西纪1781年)冬,以通渭县的石峰堡为大本营。次年,聚谋于礼拜寺中,造旗帐兵械,声为马明心复仇。四十八年(西纪1783年)四月起事,甘肃提督刚塔等讨之,田五受创死。回教徒马四圭、张文庆等,至各处散布流言,说清兵要剿绝回民,回民受此煽惑,纷起与清兵反抗;清朝乃调各处军队前往征剿。经数月之久,方克复石峰堡,回民被杀者很多。自此以后,乃永远禁止回民,不得另立新教。
新疆的回教徒,自清初平定之后,清朝对于回部,亦加意抚䘏,减轻赋税,慎选贤能之人,为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。但日久弊生,而用起侍卫和在外驻防的满员来。这班官吏,皆视此为利薮,黩货无厌,淫乱无度,威福自擅,日用服食,莫不取于阿奇木伯克。伯克亦以供给官府为名,多方搜括,从中分肥,日增月盛,乃又引起回教徒的怨恨,因之又有张格尔的反抗战。
张格尔是大和卓木布罗尼特的后裔,布罗尼特伏诛后,其子萨木克自巴达克山逃匿敖罕。萨木克有三子,张格尔即萨木克的次子。大小和卓木之乱虽平,但回教徒对和卓木的信仰仍坚,所以清朝恐怕和卓木的子孙匿处边外,终是后患,乃岁赂敖罕王银一万两,教他约束和卓木的后裔。因为如此,所以萨木克在敖罕,竟欲动不能;但张格尔颇有胆力,复以诵经祈祷,颇得各部回教徒的信仰,天山南路的回教徒闻之,渐起动摇。
到嘉庆二十五年(西纪1820年)参赞大臣斌静,荒淫更甚,回民投归张格尔者颇众。敖罕王死,而布鲁特的回民,亦怨恨清朝官吏无道,张格尔乃率领故国亡命者,投到布鲁特去,与布鲁特回民联合进袭喀什葛尔,但是未得胜利。退据那林河源,募集义军,并暗结内地的回教徒以作耳目,时掠边塞。清兵到则远遁,清兵退则又还攻,或诡词乞降,变诈百出。
道光五年(西纪1825年)九月,领队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往捕,出塞百里,未遇一敌,乃纵杀布鲁特游牧妇女百余而还。布鲁特回酋大怒,率领部众二千余追袭清兵,击杀殆尽。西回城(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)回民闻之,一时尽变。
张格尔又遣使到敖罕去乞援,约事成之后,共分四城战利品,并割喀什噶尔以作报酬。张格尔乃于道光六年(西纪1826年)率部众五百余人,由开齐山路至回城拜祭其先人和卓木的坟墓,即在此处住下。
七月,敖罕王率兵万人来援,而张格尔知喀什噶尔守兵很少,旦夕可下,欲悔前约。哪知敖罕王知道了,敖罕就把兵带回本国,张格尔复遣人追留其众,仅得两三千人来投归他,用为亲兵。八月间喀什葛尔及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皆被他攻下,他乃以和卓木的威权,调和白山派与黑山派的人民,使为己用。于是南疆的回教徒,皆服从他的命令,他的声势便更大了。但他于此时却株守于喀什噶尔,专事改革内政,并未乘机东进,以故清朝各处军队于道光七年(西纪1827年)得会集于阿克苏,向喀什噶尔进攻。张格尔亦率领各部军队迎敌,结果他的军队大败,四城皆为清兵收复。于是张格尔逃往边外山中,纠合残众,再图恢复。
张格尔本为白山派,清将乃利用黑山派的人,教他们出塞去散布谣言,说清兵已去,喀什噶尔仅一空城,回民皆盼望他回来,以诱他入塞。张格尔竟信以为真,于十二月间率五百余人进袭喀什噶尔,被清兵打败。他仅率三十余骑逃去,却被布鲁特人诱获,献给清朝。
据法国教士幼谷君之说“张格尔解送至北京时,囚以铁槛,以供众览,清帝亦欲见之。大臣等恐张格尔于帝前,陈吏治之恶弊,进以毒药,使失其口舌之能,故于帝前,口角吹沫,情形甚苦,所问之事,一不能答,遂判决寸磔之,以饲犬焉。”(见《清朝全史》下册。)
张格尔被擒后,清将长龄复檄谕敖罕、布哈尔等国,教他们将张格尔的家属献出。敖罕王遣使来说,俘掳可还,惟在回教经典中,没有献和卓木子孙的例子,因之,清朝将居于喀什噶尔的敖罕人,一齐捕获,没收其一切财产,断绝其与中国通商。
时敖罕王摩诃末阿利,亦英俊而得民心,乃要以武力恢复通商。闻张格尔兄摩诃末玉素普在布哈尔,乃把他迎来,并借兵给他,教他去收复喀什噶尔。玉素普乃于道光十年(西纪1830年)九月,率敖罕军队,及流寓敖罕、喀什噶尔人,共数万人,进攻喀什噶尔。镇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出兵迎战,被敖罕军队打败。城中白山派听说玉素普兵到,皆出来欢迎;黑山派则与清兵退守汉城。玉素普又夺得英吉沙尔,叶尔羌诸城。
道光十一年(西纪1831年)清兵援军至,会敖罕与布哈尔发生嫌隙,乃召还敖罕军队,玉素普知大事难成,亦引军西遁,白山派随之而去者约六七万人。敖罕恐清兵大举四征,想请俄国帮助,亦未成功,乃决意与清朝议和,请清朝准其通商贸易。
当时清朝提出媾和条件有二:
一、缚献贼首;
二、放还所据汉、回兵民。
后清朝亦以前次驱逐夷民与断绝贸易为失策,乃议和约让步,结果于十月间成立和约三条如下:
一、敖罕将所据中国兵民放还,并为中国监视和卓木族(惟俘献贼目事,应请免议);
二、中国仍许敖罕通商,并许其免税;
三、中国将前所抄没敖罕商民资产给还。
敖罕与清朝和约成立后,即与布哈尔发生战事。到了道光二十二年(西纪1842年)敖罕王摩诃末阿利战败而死。数年之后,王族库达雅尔嗣位,不得民心,国内悍徒,又想嗾使张格尔子弟起兵,报复前仇;于是和卓木族加他汉等七人,募集移住于敖罕的喀什噶尔人,并联合布鲁特族,于道光二十七年(西纪1847年)春,进袭喀什噶尔。而敖罕驻于喀什噶尔的事务官,亦煽惑回民使为内应,喀什噶尔乃被七和卓木所得。但各处回民,自经数次变乱以来,深以往事为戒,多数人皆不愿响应七和卓木的军队。至十一月间,清兵自伊犁来援,加他汉等七和卓木亦不战而退,喀什噶尔的回教徒畏罪与和卓木同奔敖罕者,男女老幼共约二万余人。
七和卓木乱后数年,敖罕渐渐轻视清朝,不但不为清朝监视和卓木,且常常想帮助和卓木恢复喀什噶尔。至咸丰七年(西纪1857年),窪利罕和卓木又兴兵攻克喀什噶尔,并分军侵袭叶尔羌、和阗、阿克苏等城。窪利罕在军事上虽大有进展,但喀什噶尔的回教徒,对他不满意,他将反对他的人杀了许多,于是喀什噶尔的回民人人危惧,很多人皆逃命他方。后来敖罕军队听说大队清兵回来,皆逃回本国。窪利罕亦莫可如何,也弃了喀什噶尔逃到敖罕,商民随之而去者,又是一万多人。清兵乃将和卓木同谋的人,一齐杀尽,固守边塞,严防和卓木再来入寇,并责敖罕固守前约,以约束和卓木。
回教徒对宗教的信仰甚坚,对教律的奉守甚严,因和非回教人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,致常常发生许多纠纷与冲突。纠纷发生之后,官吏方面,大多袒护非回教人,压抑回教徒,致引起回教徒的怨忿,而酿成大变,在西北方面是如此,在西南方面亦复如此。
云南的回教徒,常常与非回教人发生冲突,道光时(西纪1821~1850年)林则徐为总督,以只分良莠,不分回汉的办法,去处理回汉间的争执,云南的回教徒亦皆悦服。至咸丰元年(西纪1851年)回汉又起争执,官吏处置不公,回民大愤,上诉北京朝廷,而汉人觊觎永昌回民的腴田,与奸胥勾结,朦禀地方官吏,将所有的回人一律驱逐。回人因丧失了土地财产,常常与贵州的苗人联络,沿边滋扰,以图报复。
到了咸丰五年(西纪1855年)回人又与汉人大起冲突于临安府的铜矿,远近的回人都闻风响应,于是马金保、蓝平贵起于姚州,杜文秀起于蒙化,皆与清兵反抗,攻城侵地,大事杀戮,至同治年间方才平悉。
杜文秀是永昌回教徒的巨族,前曾反抗清朝,被清兵击败,逃匿到蒙化的围埂去。自临安事件发生后,他乃联合回民万余人,乘提督文祥攻姚州时,乃攻陷大理。咸丰六年(西纪1856年)马世德据临安,马和马贵据征江府,连下呈贡,普宁、宜良、江川等县。
适洪杨起事,杜文秀亦与洪杨有联络,故其声势颇大。至咸丰七年(西纪1857年)云南省城也被回人围攻。适当此时,不幸回人内部起了内讧,杜文秀与马先分离,马先乃投降于云贵总督张亮基。张即任其为总兵,使他率兵建功,故云南省城终没有被文秀攻下。
马先虽降清,杜文秀的势力仍大,他的族人蔡七二又攻陷顺宁、永昌、腾越等县,与缅甸接邻一带,皆归杜文秀所有。至同治二年(西纪1863年)总督潘铎被杀,省城几被回人攻陷,幸代理布政使钱毓英与马如龙(即马先)合力抵御,于是年九月,遂平定寻甸、曲靖等处。但杜文秀仍据有大理,云南省的大部分仍在他的势力之下。
到了同治七年(西纪1868年),回民又攻陷富民、安宁、昆阳、吴兴等县,杜文秀的部众,已聚三十六万人,其势力几达云南全省。他的部众又三面包围省城,至同治八年(西纪1869年),省城之围方解。清军方克复武定、大姚、征江、寻甸等县。九年(西纪1870年),攻克姚州,马金保、蓝平贵被擒;十年(西纪1871年),清兵已克复三十余城,而杜文秀仍据有大理、永昌、顺宁三府,蒙化、腾越二厅,云、赵、永、平四州县。
十一年(西纪1872年),永昌、永平、云南、赵州、蒙化等城,先后被清兵攻克。是年即进攻大理,杜文秀率部众抵御,被清兵打败,他乃和妻妾服毒自尽。清兵入大理,将他的子女及同党一齐杀尽。到同治十二年(西纪1873年),清朝方将云南回人的反抗势力,完全肃清。
当云南回民起事之后,陕、甘二省东干系的回民皆闻风响应,太平军陈得才入河南转向陕西时,河南巡抚严树森招集陕西渭、荔、泾阳等处回民六百余人,编为义勇军,不久即解散。后太平军进迫西安,团练大臣张芾等召集渭南回民首领马世贤、马四元,率回兵四百与团练共同抵御太平军。后团练败退,回兵亦逃回,而回兵所经过之处,皆被剽掠,因之回汉之间遂起猜疑。
时回民首领中有赫明堂及任五二人,在咸丰五、六年间曾举兵于云南,事败乃逃到渭南,见此情势,以为有机可乘,就暗制旗帜,联合溃军回兵,在同治元年(1862年)占据了渭南一带,团练训导赵权及绅民五百余人皆被杀。
张芾奉清朝命令到临潼去劝谕,也被任五所杀。回兵乃围攻同州,犯西安,清朝知招抚已无效,乃派钦差大臣胜保及多隆阿等率兵入陕征讨。到了同治二年(西纪1863年)方告平定,但回民余党多逃到甘肃,与甘肃的回民联合,而与清兵抗战。
甘肃方面回汉之间,也时常发生仇杀事件。同治元年七月,凤翔的回民杀汉人,围郡城。次年正月,甘肃回民起于平凉,进陷固原,陕甘总督熙宁讨之未胜,多隆阿至西安后,率兵西征,回民败走甘肃,适宁夏回民又与汉人发生争执,攻陷宁夏及灵州,首领马化龙(即马明心所创之新教教主)被回民迎入宁夏。时马彦龙,马占鼇起于知州,攻陷狄道。马桂源,马本源起于西宁,逐总兵知府。其后马文禄据肃州,自称兵马大元帅,各地纷纷变乱,甘肃竟无完土了。而云南蓝大顺又入陕,占据盩厔,多隆阿复回兵攻蓝,因之甘肃回民的势力益张,盩厔光复后,多隆阿亦阵亡。后清兵入甘,于同治四五年间,与回民激战,互有胜负,至同治六年(西纪1867年)六月,清朝乃命左宗棠总督陕甘二省,率兵大举西征。
左宗棠于同治七年(西纪1868年)十月到西安,遂定南、北、中三路进讨之策。北路由绥德取道花马池,直捣金积堡,以刘松山当之;南路由泰州趋巩昌,讨河、狄之回教徒,以周开锡当之;中路由左亲率刘典诸军,尽将陕西的回民驱入甘肃。
北路进展甚速,连战皆捷,马化龙数次迎战,皆被刘松山打得大败,遂托于甘肃的回民而乞降。因之,由陕西逃出的回教徒益不自安,皆向西逃。首领白彦虎、禹得彦、李经举、崔三等,想至河州与南路回民联合,被清兵追击,杀死千五百余人,刘松山亦克复灵州。
八年(西纪1869年)十一月,左将大营移住平凉。九年(西纪1870年)正月,进攻马五塞,刘松山中弹阵亡,马五塞亦被攻克。刘松山死后,马化龙的势力又大,崔三欲分清兵之力,突入陕西,后被击退。
九年(西纪1870年)东自吴忠至灵州间堡寨四百五十余,西自洪乐堡至峡口,堡寨一百二十余,皆被清兵平复。马化龙的大本营金积堡也被攻陷,马化龙被杀,宁夏的反抗战乃告结束。
十年(西纪1871年)五月,左宗棠又率诸将征讨河州回民,七月移大本营于静宁,八月又移安定,先下洮东的唐家涯,后又攻克洮西的三甲集。十月,黑山一带延袭数十里的大小回垒皆平复。十二月棠川的回垒皆投降。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初逃至牟尼沟,再逃至太子寺,终于十一年(西纪1872年)正月请降,河州的反抗战亦告平复。七月,左宗棠进驻兰州,仍命诸将西征。
是年冬,刘锦棠大败回军于西宁及大通,自此以后,回教徒的首领如崔三、禹得彦等,多请归降;独白彦虎率残众由永安入肃州。肃州马文禄(即马四)、马长顺勇而善战,招纳渭南、金积、河州、西宁,各处战败的回民,声势亦颇浩大,守战多时,后亦归降,被清兵所杀,而白彦虎则逃到喀什噶尔去了。
当陕甘回乱发生的时候,新疆的回民又成立了两个王国,一个是清真王国,一个是喀什噶尔王国。清真王国的首领是妥明(又叫妥得邻),他本是陕西回教徒中的一个阿訇,当陕乱起时,赴各处煽动,后至乌鲁木齐,参将索焕章以师事之。因索亦素畜异志,故妥明在回民中的势力颇大。州役马金、马八,皆是东干系的回教徒,假都统的命令,到处搜刮汉人。汉人大愤,乃结团练和他对抗。马金、马八亦纠合回教的人大战于奇台市。
适南路库车的回教徒马隆,聚众推黑山派的和卓木布格聂丁为首领谋叛,清军讨之屡败。于是索乃乘此机会,推妥明为主,自号元帅,于同治三年(西纪1864年)六月,据乌鲁木齐反叛。九月陷满城、奇台、绥来、昌吉、阜康诸县,而哈密、吐鲁番、克尔哈剌斯,亦在东干回民势力之下;布克聂丁亦领兵南进,攻克喀喇沙尔、阿克苏、乌什、叶尔羌。清兵所守者,仅喀喇沙尔、英吉沙南城,而回教徒金相印亦起于喀什噶尔,更引敖罕的安集延兵以自助。敖罕乃以和卓木布士尔克(即张格尔之子)率将雅克布白克东来,至喀什噶尔,布士尔克乃即王位,以雅克布为辅佐,使他专任军务。
雅克布有才略,好功名,乃募集新兵,以资御防。雅克布使布士尔克围攻喀什噶尔的汉城,他自己率兵攻取英吉沙尔、叶尔羌,但被东干回兵打败,仍退至喀什噶尔。东干回军想趁势一举而夺喀什噶尔,去请布格聂丁来帮助,后皆被雅克布攻破,于是军威大振,喀什噶尔的汉城,亦被攻下。又移师东窥叶尔羌,奇卜察克族皆嫉其专权,与和卓木华黎汉谋,想除去之,被他知道,而回军肃清反对党。
待内乱平定之后,又出兵东向,攻克叶尔羌,夺得和阗,回疆四城皆为他所有,于是他力劝其王布士尔克到麦加去朝觐。他在同治六年(西纪1867年)即王位,称毕调勒特汗。布哈尔王闻之,赠以达利克格吉的尊号(意即能征讨不信者的荣誉教父)。
时黑山派的和卓木布格聂丁在库车,阿克苏以东皆受他统治,雅克布即进兵攻阿克苏。布格聂丁被他打得大败,库车、克尔喀喇沙尔等城,皆被他攻下,乃与清真王妥明划界,以喀喇沙尔以东十二三里归还于喀什噶尔。
当妥明在乌鲁木齐起事之后,北路汉人皆组织义勇军与妥明对抗,迪化的徐学功最有勇略,召集义军五千,以防妥明。同治八年(西纪1869年)妥明欲制止雅克布东进,命马泰为将,率乌鲁木齐即吐鲁番兵七八千进兵库车。雅克布率兵来援,大破东干回军,乘胜至克尔喇。雅克布与义军首领徐学功议和,同攻妥明,乃于九年(西纪1870年)闰八月攻乌鲁木齐。妥明逃到绥来,不久即病死,东干系的势力亦消灭。
当此时,俄国乘新疆各派回教徒相互纷扰的时候,乃占领伊犁。雅克布本想进攻伊犁,知俄人势不可侮,乃还喀什噶尔,从事于内政的设施。天山南路及北路的乌鲁木齐,以西至马纳斯,都奉行他的命令。
到了光绪元年(西纪1875年)清朝又命左宗棠出兵西征,次年五月,先行刘锦棠至巴里坤,进夺古城,分兵屯木垒河。时马人得据乌鲁木齐,白彦虎据红庙子,马明据古城。六月刘锦棠部克复乌鲁木齐、昌吉、呼图壁等城,天山北路略定。
时雅克布据托克逊、筑三城以自卫,乃分兵守吐鲁番。达板、乌鲁木齐的败兵皆逃到达板,白彦虎亦逃到托克逊。是年冬,雅克布移住喀喇沙尔,使白彦虎马人得守吐鲁番,海克拉守托克逊,大通哈守达板。
光绪三年(西纪1877年)清军即由乌鲁木齐进攻达板,由哈密进攻吐鲁番,不久皆被清军攻克。清军又进袭托克逊三城,也皆被克复。南八城连年战争,租税日重,人心离散,雅克布知大事已去,乃饮药而死。其次子海古拉,把他的尸身送到库车,但中途被马子艾哥(伯克胡里)劫去,海古拉亦被杀。
马子艾哥遂据喀什噶尔即王位,使白彦虎守库尔勒,后白彦虎亦逃到俄国境内去了。清军乘胜南进,攻克喀什噶尔城,天山路悉平。自此以后,回教徒反抗清朝,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声势了,如光绪二十一年(西纪1895年)甘肃回教的反清,二十二年(西纪1896年)新疆回教徒的反清,皆不久消灭。
清初,平定回部以后,葱岭以西各回教国家,亦皆与中国发生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关系,如敖罕八城(亦作浩罕、霍罕,所属有敖罕、纳细木、玛尔葛郎、安集延四大城;窝什、霍克占、科拉普、塔什干四小城,故称敖罕八城),因中国断绝其贸易,尤其是禁止茶与大黄出口,使敖罕大起恐慌,安集延人来中国经商贸易者则更多。
至于政治上关系,亦颇复杂,尤其是敦罕,曾数次帮助和卓木反抗清朝,敏罕的军队,也常常随和卓木转战于新疆各地;布哈尔,布鲁特等国,也曾经帮助过和卓木入新起事。巴达克山(清代的书中都称为城郭回回)、克什米尔、乾竺特(即坎巨提,亦称喀楚特)、博罗尔、阿富汗(亦称爱乌罕)、哈萨克(共分三部,左都额尔图玉斯,俄人称为大吉尔吉思;中部齐齐玉斯,俄人称为中吉尔吉思;西部乌拉玉斯,俄人称为小吉尔吉思)等部,都每年一次或数年一次来中国朝贡。哈萨克的部长,清初曾授以王公台吉的称号。布鲁特的头目,亦授以二品至七品的官衔,其与中国的关系,亦可想而知了。

1
